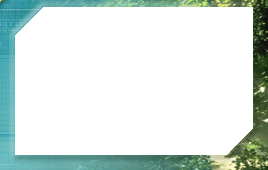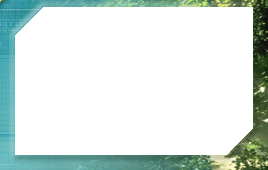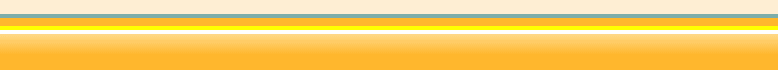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关 键 词:甲午战争 东亚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战前,英国势力的存在和中国看似强大的国力,一直维持东亚地区的脆弱均势,而日本在战争中的速战速胜一方面将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勾引起欧美各大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欲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也令这些大国对日本刮目相看,使日本一跃而为东亚霸主,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被彻底解除。从此,东亚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多事之秋,各国围绕争夺东亚展开新的角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东亚地区才重新达成新的均势。
在这场改变东亚局势的战争中,美国的表现似乎没有英、俄、德、法等国家突出,始终声称奉行“中立”政策,实际上却发挥了其他列强不曾起到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①利用国内外已出版的中、美、日、法等国的外交文件及相关文献,就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所做的反应及扮演的角色和原因等做一专题研究,希望对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和晚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有所推展。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战前美国对朝鲜问题的观察和反应
由于朝鲜在东亚的特殊地理位置,朝鲜问题在19世纪中叶就被纳入美国的东亚政策之中。19世纪60年代,美国成功叩开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主要国家的大门之后,便有意染指朝鲜,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和日本势力的一个跳板。1871年5—7月,美国亚洲舰队司令率5艘军舰入侵朝鲜,但被朝鲜军民击退。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再次激发美国进入朝鲜的愿望,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 Seward)认为从“日本的胜利中看到了使美国得到一个条约的机会”,并建议美国政府签订与日本类似的朝美条约。②1878年底,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薛斐尔(R. W. Shufeldt)前往东亚执行这一使命。1882年5月美国与朝鲜签订修好通商条约,成为西方列强中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朝鲜向西方国家敞开大门的国家。
1894年春,朝鲜国内发生东学党起义。6月1日东学党占领全州后,朝鲜国王决定向中国借兵代剿,并于6月3日正式照会袁世凯,提出借兵请求。次日,清廷便批准李鸿章的派兵赴朝计划。6月6日,清政府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将中国派兵赴朝一事照会日本政府。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借兵的消息后,日本政府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为日本蓄谋已久的出兵朝鲜提供借口。在中国通报派兵的次日,日本即按预订方案,也将出兵朝鲜的决定正式照会清政府。但在清朝军队与朝鲜农民起义军交战之前,朝鲜政府6月11日便与发动起义的东学党人订立《全州和约》,平息了农民起义。6月13日朝鲜政府致函袁世凯,要求撤回清朝军队。清朝政府表示愿意从朝鲜撤兵,但要求日本也同时撤军。而日本政府则拒绝撤军,以朝鲜完成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方案作为撤兵条件,并不断制造事端,增兵朝鲜,将中日撤兵问题逐步引向其与中国开战、独占朝鲜的预定轨道。
对于因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所引发的紧张局面,美国驻朝鲜、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官从一开始就予以密切关注。1894年6月18日,美国驻朝公使西尔(M. B. Sill)向国务院报告,日本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汉城“肯定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指出:“现在很显然,日本人已经到了这里,他们可能会坚信他们不能‘有失面子’地离开这里,他们或许会喜欢有一个宣称他们在韩国的影响的机会。”同时,西尔将朝鲜出现的紧张局面归咎中国,声称:“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错误很显然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行动,他们将军队派到朝鲜;如果中国没有这样做,日本派来的军队可能就会少许多,或者不会派遣任何军队。”他还表示,鉴于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有100余名日本人伤亡,而目前在朝的日本人超过10000人,因此日本方面解释派军入朝是为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人和使馆,“是相当合乎情理的”。③在6月29日的报告中,西尔又对日本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撤兵条件和要求解除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明确表示支持:
我可以说,日本对于朝鲜似乎是很善意的。日本似乎仅希望朝鲜永久摆脱中国宗主权的支配,然后通过帮助朝鲜进行把和平、繁荣和开明带给它的人民的改革,以此来帮助这个日本的弱邻,巩固它的独立地位。这个动机受到了许多比较有知识的朝鲜官吏们的欢迎,并且我想象在美国也不会遇到反对的。④
美国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同样站在日本一边。他虽然在6月15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本在朝鲜部署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不可能仅为保护使领馆及侨民,如果不是对中国威胁的话,至少也是想展示日本的力量,表明它有能力在朝鲜组织大量军力,以免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威胁朝鲜主权的完整。他断言:日本民众对中国在朝鲜影响力的强烈忌恨,很有可能促使日本政府采取行动,危害中日两国的和平关系。⑤但7月3日复电报告造成中日关系紧张局面及解释日本派兵的原因时,谭恩完全赞同日本政府的解释,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和朝鲜,谓:日本外务大臣向他保证派军队到朝鲜首先是根据1882年的《济物浦条约》,而中国派兵的照会使得日本增兵成为必然,以避免1882-1884年事件再次发生;朝鲜所发生的叛乱是由于腐败和压迫,为确保未来的和平,日本要求朝鲜进行激进的行政改革,并建议与中国一道实现这一目标,但遭中国拒绝,因此日本将不顾中国的反对,单独推行这些改革;日本没有任何侵略领土的意图,现在必须由中国做出一些友好表示。⑥
7月7日美国政府致电对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表示遗憾之后,谭恩继续为日本辩护。7月10日,他向美国政府转达日本关于朝鲜政策的表态:
日本在朝鲜的目的并不是要制造战争,实质上是为了确保朝鲜的主权、独立、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治,以避免再次发生叛乱。日本期望消除官场腐败、贪污和各种弊政的根源。朝鲜政府应该实行我们建议的改革,中国的含糊态度妨碍了这些改革,并危害东亚的和平。叛乱并没有完全平息,它的根源依然存在。日本此时撤兵是不明智的,一旦未来的和平得到保证,日本会即刻撤兵,不存在任何与朝鲜发生战争的忧虑。
随后,谭恩附和日本的说法,声称:“我个人认为中日之间不存在爆发战争的任何可能性。”⑦7月14日,他又给美国政府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再次声称日本在朝鲜的目的不是要发动战争,只是想对朝鲜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朝鲜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实现自主和主权独立”。他说:“我与陆奥先生就朝鲜问题做过数次晤谈,没有理由怀疑日本目前在朝鲜所采取行动的动机和政策”,他强调日本政府受国内民意的压力,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能后退,必须达到目的,“如果日本目前在没有获得与出兵规模和支出相称的目标或好处时即从朝鲜撤兵,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反对情绪”。⑧不难看出,谭恩实际上是建议美国政府接受和支持日本的朝鲜政策。
美国驻华署理公使田夏礼(Charles Denby,Jr.)由于身在中国,在甲午战前比较客观地报告了日本主动挑起战争的事实。如在6月8日的报告中,他指出清朝出兵朝鲜系“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主要是为了避免叛军逼近汉城”,“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向日本和俄国保证,一旦叛乱平息,清朝方面立即撤兵”。⑨7月3日电告围绕朝鲜问题的敌对行动“已迫在眉睫,尽管日本采取进攻行动,但中国方面仍显示妥协态度,请求英国和俄国的调解,争取和平解决”。⑩但这并不表明他的立场站在中国一边。田夏礼当时之所以没有像西尔和谭恩那样支持日本发动战争,主要在于他认为日本不可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胜。(11)
对于中日出兵朝鲜所引发的紧张局面,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比较微妙。一方面,由于战争结局及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当时在东亚的势力有限,将无法主导局面。因此,美国政府开始时并不愿意看到日本因朝鲜问题挑起战争,致使东亚局面复杂化。6月22日,国务院致驻朝公使西尔的电文训令就表达了这一愿望,称:“出于美国对朝鲜及其人民的福祉的友好的关怀,兹依总统的指示,训令你竭尽所能来维护和平。”(12)6月29日,国务卿葛礼山(W. Q. Gresham)又致电驻日公使谭恩,表示鉴于美国对日本和朝鲜两国都抱有友好感情以及朝鲜目前的无助,要求谭恩弄清并报告日本派兵到朝鲜的原因及日本对朝鲜所提的要求。(13)7月7日,葛礼山再次致电谭恩,对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兵,并要求改革朝鲜内政表示“遗憾”,称:“朝鲜国变乱尽管业已归于平定,但日本拒绝撤兵,并要求对该国内政施行急剧改革,合众国政府闻之深表遗憾。且清国有希望日清两国同时撤兵之事,如有上述要求更引起他人之注目。合众国政府对日本、朝鲜两国怀有深厚友谊,故希望朝鲜国独立和尊重其主权”,并指示谭恩转告日本政府:如日本政府向不堪防守的邻国施以不正义的战争,大总统将痛感失望。(14)
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拒绝朝鲜和清政府的调停请求,听任日本因朝鲜问题发动战争。1894年6月24日,朝鲜政府致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朝公使,请求各国政府出面斡旋,敦促日本从朝鲜撤军,指出:“在日本与朝鲜和平相处的时候,朝鲜境内保留这样多的日本武装军队是不合乎国际法的。”(15)在6月26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谒见朝鲜国王,拒绝撤退日本军队,并逼迫朝鲜进行改革内政之后,朝鲜政府又接连二次致电驻美公使李承寿,请求美国出面斡旋。(16)
对此,美国国务卿只是一般地对朝鲜的处境表示同情,希望朝鲜的主权得到尊重,但拒绝朝鲜政府的斡旋请求,表示美国必须保持对朝鲜和其他国家“一个公平的中立态度,我们仅能以友好的方式予日本以影响,我们绝不能够同其他国家联合干涉”。(17)
尽管出于各种原因,美国政府7月7日致电美国驻日公使,对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兵表示遗憾,但这只是为应付舆论和其他国家的斡旋建议而表示一种姿态而已。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当时就已看出美国的意图,指出:“美国为从来对我国友谊甚厚,最抱好意之国,从彼国固有之政略上言之,尤不好容喙于远东之事件,究不过难拒绝人类普通爱和平之希望及朝鲜之恳求,故发此劝告,此外无他意也。”(18)事实确如陆奥宗光所分析的那样。7月8日,英国驻美大使授命询问葛礼山是否愿意与英国一道联合干预,以避免中日爆发战争,后者就表示,美国奉行友好的中立政策,不会进行干预;美国已向日本方面做过调停,不可能进一步斡旋。次日,葛礼山还特意将7月7日美国政府致驻日公使谭恩训令的一份复印件交给英国大使,并强调即使是友好的调停,美国也不会参加。(19)7月13日,中国驻美公使面晤葛礼山,请求美国出面与其他国家联合,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军,制止日本发动战争,葛礼山也以同样理由拒绝,声称美国在7月7日向日本发出规劝之后,“我们看不出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不可能与其他列强联合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他还违心地单方面听信日本方面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的说法,认为日本不会发动战争,指出“从谭恩及其他方面收到的情报看来,我难立即相信日本将诉诸战争”。(20)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美国一方面以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和日本不会发动战争为理由,拒绝在中日间进行斡旋,另一方面却对日本提出的战争爆发后由美国代为保护在华日本人的请求慨然应允。早在6月底,日本为发动战争就询问美国政府,一旦日本公使撤离北京,美国是否愿意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及财产,(21)葛礼山当即回复表示,如获中国认可,日本的这一请求将受到“总统的善意考虑”。(22)7月13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的密函中就通报了日本方面已与美国商定,如获得清政府同意,美国愿意在中日开战时代为保护在华日本商民。(23)8月1日,美国驻华署理公使田夏礼收到日本驻华公使小村请求代为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函件后,当日即照会总理衙门,宣布自即日起,战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均在本署大臣及本国驻各口领事保护之下”。(24)
与美国事先私下商定后,日本政府为诱使清政府同意战时由美国代为保护在中国的日本商民,便放出有关风声。1894年7月16日,清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清政府,建议请美国政府保护在日本的中国商民,指出日本已约请法国代为保护日本在华商民,中国在日商人求护日切,美使接本国政府电报,如中国政府托美护商,美国愿意效力。(25)鉴于中日开战已不可避免,7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美署理公使田夏礼,正式请求美国对在日华民“按照公法代为保护”。(26)8月2日,田夏礼照会清朝总理衙门,表示中国请美国保护侨居日本中国人一事已获本国政府同意,并已电令美国驻日本公使“于中日开仗时保护住日本之中国人矣”。(27)
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前一方面以日本不会发动战争和声称奉行中立政策为由拒绝斡旋,但同时又欣然接受战时保护人角色,这只能说明美国政府其实已知战争不可避免,并乐于看到中日交战。
二、美国政府与日本间谍案
中日宣战后不久,8月4日清政府在天津逮捕一个名叫石川伍一的日本间谍。8月6日总理衙门照会田夏礼,表示将根据国际法惯例,对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予以惩处。照会称:
顷接北洋大臣电称,倭人在津日派奸细二、三十人,或改装薙髮,潜往各处窥探军情等语。查公法第六百二十七至六百四十一条论处治奸细之罪甚严,现既失和交战,其安分商民自应照约保护,而此等奸细不在保护之列,亦必从严惩治,以符公法。(28)
对这一合理要求,田夏礼极力抵制和反对,8月8日在回复照会中警告清政府对日本间谍要严加甄别,不要制造错案,说“缘此等事情最易办理过情”,“现在中日开仗系在朝鲜,中国地方并无日本一兵一骑,据想即系实有日本人来作奸细之据,如遽行严惩,亦非切当办法”,提议如有日本人在内地从事间谍活动者,请解交就近海口,驱逐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矣”。要求清朝政府“本仁慈之心,不因两国失和,于日本人民恨恶而深绝之可也”。(29)
对田夏礼这一偏袒日本、危害中国安全的要求,清政府断然拒绝。8月12日,总理衙门复照田夏礼,明确表示其建议与公法不符,对中国安全构成危害,坚持按6日的照会精神办理。(30)
除向总理衙门建议外,田夏礼还指示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Sheridan P. Read)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交涉。8月29日,李德致函李鸿章,要求释放石川伍一,称:“石川伍一并非奸细,本大臣应请中堂开放送交驻津李领事转饬回国。”(31)李德这一要求遭李鸿章拒绝。9月4日,津海关道盛宣怀代表北洋大臣复函李德,驳斥日本方面所谓石川非间谍一说,指出根据中日修好条约相关条款,两国商民均不得改装衣冠,“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此前贵领事声称所有在天津的日本人均已随同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回国,“何以该犯石川独不同行,且不令贵领事知其住处?”坚持“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查根究,未便遽行开释”。(32)9月10日,总理衙门就此事再次照会田夏礼,重申日人石川“似不在保护之例”,要求田夏礼停止干涉,转达驻津领事“勿再误会,致倭奸恃为护符,幸逃法网”。(33)
继在天津逮捕石川伍一之后,清朝政府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查获一些日本间谍。8月14日,上海道在上海法租界起获两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以日本人归美国保护,交美署管押。对于这两名日本间谍,美驻沪总领事佑尼干(T. R. Jernigan)和田夏礼也曲意加以保护。佑尼干以事关重大、须电美公使指示和“案情长冗,须用详文,未便电禀”等为由,拒交日本间谍。(34)田夏礼则以“本署大臣现尚未接到该总领事详报,无知悉此案详细情形,是以未便遽照所请饬行办理”为词,虚与应付。(35)
对于美国公使和上海总领事为拒交日本间谍而演出的双簧戏,清政府于20日再次照会田夏礼,进行严正交涉,谴责他们的做法违背中立,“于中国防务大有关碍,殊乖两国睦谊”,敦促田夏礼“电饬该领事,迅将此案情形报明贵署大臣查照,一面先将所获倭人二名送交上海道审明惩办,以符公法而重邦交”。(36)同时,清政府指示驻美公使杨儒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8月20日,杨儒致电总理衙门汇报交涉结果,称:“顷晤外部,据云奸细如有确据,领事不应袒护,惟来电情节未晰,已电询田使。”(37)而根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显示,事实是在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向美国政府交涉后,葛礼山8月18日致电田夏礼询问日本间谍案情况,21日田夏礼便复电作了汇报,同日,葛礼山即致电田夏礼,指示他们交出日本间谍,表示在中国的美国公使馆和领事馆没有授权收留被指控违背中国政府的日本罪犯。(38)
虽然葛礼山已指示交出日本间谍,但田夏礼还是一再拖延。21日,田夏礼照会总理衙门,推托待接到美国政府的具体指示后即行交出,称:“本署大臣已知中国将此事电行驻本国杨大臣转达外部,现接外部来电,嘱将此案细情即行电转。兹已按所知情形电复矣,应俟本国外部将此案如何嘱办,再行办理。是以请贵王大臣俟本署大臣接有外部如何电嘱,自必即行照复。”(39)
8月23日,驻美公使杨儒将葛礼山21日致电田夏礼的指示通报总理衙门,谓:“接号电又晤外部,知田使复电亦到。据葛云,奸细应交,美使及领事袒宕非是,已电田使饬交。”(40)次日,总理衙门便根据杨儒的报告,再次照会田夏礼,要求他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交出日本间谍,称:
上海拿获日本奸细一案,迭经本衙门照会贵署大臣转饬驻沪领事速交在案。兹本月二十三日接出使贵国杨大臣二十二日电称,屡晤贵国外部葛大臣。据云贵署大臣复电已到,并称奸细照例应交,领事不应袒宕,已电贵署大臣饬领事交出等语。应请贵署大臣即遵贵国外部之意转饬驻沪总领事,速将日本奸细二名照交中国地方官审办。(41)
但田夏礼继续以等待指示为由进行拖延,8月27日照会总理衙门,谎称:“本署大臣于二十五日下午已接到本国外部来电,内系仍欲详知此案情形,经于二十六日具电声复,请外部即实行饬知此案应如何办理,想今明二日内,定有外部电复。俟接到时,自当知照贵署即行照办也。”(42)
如前所述,国务卿葛礼山于21日就指示田夏礼交出日本间谍,田夏礼在给总理衙门照会中所谓的8月26日的具文声复,事实上只是试图说服葛礼山改变此前的指示,同意他们拒交日本间谍,声称这两个日本间谍“只是在校学生,公开、和平地在上海居住”,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改穿中国服装虽与条约规定不符,但并没有遭到反对,请求葛礼山同意由美驻沪总领事作为仲裁人和一名中国官员一道听审,并居然表示外国人犯罪不应由中国政府来处罚,试图让日本间谍享有治外法权。(43)
然而,美国政府鉴于庇护日本间谍明显违背中立政策,并没有接受田夏礼的意见。8月29日,葛礼山致电田夏礼,明确指示他在处理日本间谍问题上应保持中立,遵守美国政府指示,将日本间谍交清政府处理,电文称:
目下中日交战,不相通使,该代办乃局外邦国使臣,理宜不偏不袒,而所行所办,中倭均应视为公道……此意应切念之,务当遵照公法,而不失局外邦国之谊。美国不得视倭人为美民,亦不得使倭人向无享受如此利益者,而不归中国管辖,亦不得留之治以美例,统归美使领事管理,亦不得将使署、领署作为倭人避法之区。总之倭人仍系倭国子民,应照向来办法,归地方官审办,不得因美官保护而稍有变迁。(44)
在葛礼山下达如此明确指示后,田夏礼还试图做最后努力,以保护两名日本间谍。8月31日,他再次致电葛礼山,称:美国驻日公使来电,声称日本政府保证这两名日本人不是间谍,并要求中国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回到北京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您是授权我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还是命令立即无条件地将两名日本人交给中国政府?”田夏礼这一不执行命令的做法显然令葛礼山极为不悦,他当即复电,指出“我29日的指示已十分清楚。”(45)
总理衙门也于8月31日在接到驻美公使杨儒关于葛礼山8月29日电文指示报告后,(46)当即照会田夏礼,揭露他此前照会内称各节“核与杨大臣电述贵国外部之意两歧”,要求田夏礼根据美国政府指示,速饬上海美领事将日本间谍交上海道惩办。同日,总理衙门还就美国驻汉口领事保护逃入租界、伪装华人的日本人照会田夏礼,提出抗议,并谴责田夏礼庇护上海日本间谍的行为助长了在华日本人的间谍活动,指出:
查中日未经失和以前,条约内载两国商民不准改换衣冠,致滋冒混。是平时倭人改易华装,尚干例禁,况现当两国开战之际,倭人改装薙髮,匿居中国,其为窥探军情,有心混迹可知。此次汉口之改装倭人,一经营勇盘诘,即持刀抗拒,逃入租界,情弊显露。而美领事讳为日本安分之人,即时送沪,是否有意袒庇倭奸,殊难剖白。但论公法,似已未协,且于贵国保护真正安分商民之名有损。盖缘沪关所获倭奸,不早交出讯办,以致他口倭奸效尤无忌,实于中国军情大有妨碍。应请贵署大臣严饬各口领事,嗣后如遇此等情事,即照公法交出讯办,以敦睦谊可也。(47)
最后的努力失败后,田夏礼只好于9月1日照会总理衙门,通报已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致电驻沪总领事佑尼干,令他交出日本间谍。(4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田夏礼和佑尼干附和日本政府说法,称在上海法租界拘捕的两名日本人并非间谍是毫无根据的。两名日本人被引渡后,其身份也被查明,一个名为福原林平,另一个名为楠内友次郎,是奉日本军方之命,计划从上海北上营口,探听军情。为避人耳目,8月10日从上海日人居住地瀛华广懋馆移居中国人在法租界开设的同福客栈,准备候船北上。由于两人举动异常,形迹可疑,引起上海道密探的注意,遂于14日被租界巡捕拘捕,并从他们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与日本军方联络的暗号和电报密码。因此,福原和楠内系日本间谍确实无疑。(49)并且,通过他们的招供,还侦破8月19日在浙江拘捕的两名日本僧人高见武夫和藤岛武彦也同为日本间谍。(50)查明真相后,福原林平、楠内友次郎、高见武夫和藤岛武彦先后被处决。
尽管在上述日本间谍案的交涉中,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美国驻华署理公使田夏礼还是成功帮助一个名为川烟丈之助的日本间谍逃避清政府的拘捕,安然返回日本。川烟丈之助原为步兵少尉,1892年9月间由日本派往中国从事侦察活动。他在奉天一带活动近两年,到处搜集情报,发回日本国内,对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发动辽东战役立下功劳。1894年8月间,他由东北经烟台转赴北京。8月31日,田夏礼突然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发给川烟丈之助路照,使之“执持赴津”回国,谎称川烟丈之助系一位美国传教士所开学堂的学生,“两月前该学房放热学时,该学生即外出游历,昨于七月三十旋回学房,仍欲入学,伊尚不知中日业已失和。该教士因际此时不愿留此日本学生,欲其回国”。(51)总理衙门虽然在9月2日的复函中认为田夏礼函中所说的有关川烟丈之助的情况不可信,破绽百出,但顾及在日本的中国侨民需要美国外交官代为出面保护,因此在川烟丈之助回国问题上又不愿过于得罪田夏礼,留了退路,要求在说明川烟丈之助“何年来京附学”和“本年避暑往来踪迹”后,“再与贵署大臣商办”。(52)
接到总理衙门的回复后,那位美国传教士立即就为川烟丈之助编造了来京附学的时间及暑期游历行踪,并称“该日本人系极好学生,并甚朴实”。田夏礼也在9月5日致总理衙门函中为其担保,称:“查该教士人品向来方正,以上所言实为可靠;仍请贵衙门大臣查照,缮给该日本人川烟丈之助由京赴津之护照,俾其平安抵津。”(53)9月13日总理衙门致函田夏礼,同意放行,准其出境。在田夏礼的安排下,这名日本间谍终于在10月4日从上海乘船回国。(54)
中日开战后,美国受两国的委托,代为保护中日两国在对方国家的侨民,这本符合正常的国际法惯例。然而,美国外交官在保护在华日本人中却常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对日本在中国的间谍也试图加以保护,这就暴露了他们袒护日本的立场。在日本间谍案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的立场与驻华外交官有所区别,基本信守了中立政策,但这并不足以整体上否定甲午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亲日立场,这在此后美国政府在调停中日战争的过程中反映得更为清楚。
三、美国的第一次调停
中日围绕朝鲜撤兵问题发生之后,清政府始终无意与日开战,曾请求俄、英和美、奥、意等国加以干涉或调停,避免中日爆发战争。9月15日平壤战败后,清廷内议和之声再起。9月27日,慈禧太后命翁同龢前往天津,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调停。10月初,清朝总理衙门官员奕劻、奕訢等多次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会谈,商议由英国出面调停,并提出以保证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作为讲和条件。10月末,在英国的调停建议遭日本拒绝和日军侵入中国本土之后,清政府转而请求美国出面调停。10月31日,恭亲王奕訢和孙毓汶、张荫桓等总理衙门官员专门约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举行密谈,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1款内容,请求美国充当调解人,致函日本,建议停战,最终缔结和约。(55)11月3日,总理衙门又迫不及待地召见美、英、法、德、俄五国公使,提出同意承认朝鲜独立和向日本提供军费赔偿作为和谈条件,请求各国公使建议本国政府出面调停,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当日致美国政府的电文中称:“今日总署召集英、法、德、俄各公使及我本人开会,要求我们电请我们的政府出面干涉,获取和平。它提出谈判的基础为朝鲜独立和分期赔偿战费(数额由友国共同决定)。”(56)
在议和问题上,一方面,美国政府以保持中立为由,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早在10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指示驻美代办歌珅(W. E. Goschen)致函国务卿葛礼山,询问美国是否愿意与英国、德国、法国和俄国一道调停中日战争,并指出调停的条件是由各列强保证朝鲜的独立,日本将获得一笔战争赔款,(57)美国政府就予以拒绝。葛礼山12日复电表示,美国总统虽然真诚希望中国和日本尽快达成和平条件,并不使朝鲜蒙羞,但他不能接受参加四国干涉的要求。(58)即使英国政府做出进一步解释,表示五国的调解活动将“仅限于外交的行动,并将仅于有适当机会采取这一步骤时进行”,(59)但“这个声明并没有变更总统的判断”。(60)并且,葛礼山还将这一情况秘密通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栗野在10月22日发给日本外务大臣的电文中写道:“国务卿以如下之事密告本使:英国政府询问美国政府关于为恢复和平试图干涉一事,是否有与英、德、俄、法同盟之意。美国政府则以同欧洲诸国结成关系,与美国之政策背道而驰拒绝之。”(61)11月8日,法国驻美大使巴德诺(Patentre)代表法国政府,建议美国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中日战争,葛礼山也坚决予以拒绝,声称“美国不能加入一项旨在迫使日本接受它事先不准备同意的条件的干预活动”,清政府“只是在看到他们的提议遭到日本人拒绝后才向列强求助,以便列强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因此,不能同意清朝政府的请求;并表示既然中日交战双方可以直接进行谈判,列强也就没有调停的必要。(62)
另一方面,美国又力图出面单独调停,操纵和谈。11月6日,葛礼山致电驻日公使谭恩,照会日本政府,表示美国愿意为结束目前战争出面单独调停,询问:“日本国政府是否承诺?”(63)为达到单独调停的目的,葛礼山同日又致电田贝,极力阻止和压制清政府向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指出:“中国致欧洲各大国同样请求,也许将多少阻碍总统的行动自由”,“总统谢绝任何共同的干涉。我今天训令你行动,大体上可以说已经是在中国请求之先提出了调停。总统希望很快知道他今天提出的他单独的调停,是否为交战国双方都可以接受的。”(64)接到美国政府的指示后,田贝7日前往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施压,强调美国只有作为唯一的调停者才会出面斡旋,要求清政府停止向其他国家寻求调停,指出:总署对美国作特别的请求,但同时又请其他五国为中国出面干涉,这种行为是互相矛盾,并且是令人感到困惑的。(65)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决定出面单独调停中日战争,表面是响应清政府的请求,但实际上更大程度是为日本减轻来自俄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外交压力。葛礼山对此直言不讳,在向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解释美国出面调停的原因时,明确表示系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目前欧洲各国欲联合干涉中日战争,结果将对日本不利,因此,美国总统完全出于对日本的友谊,愿意对中日两国进行公平调停。(二)自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方面在海陆同时连战连捷,并进入中国本土,逼近北京,日本国之武威已光耀宇内,跃居世界强国之一,美国此时出面调停,对日本的名誉毫无损害。(三)如日本因受各国压制而与英国或其他一、二盟国发生战争,虽与美国无关,但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般情谊偏向日本一边,因此美国届时是否仍严守中立而为局外旁观者,乃为美国政治家必须考虑的一件大事。(四)美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友谊的调停过程中,将绝不允许英国插手。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当即感谢美国“对帝国之厚情”,表示“急速电告本国政府相答”,(66)建议日本政府“应听从合众国之调停,因为该国之舆论不仅大为偏袒日本,且大总统亦因国内策略与其一己之友情,始终尽力于使日本满意之事”。(67)
日本政府虽然认为美国将是日本与中国和谈的最好中间人,但并不愿接受美国的调停建议,使中日谈判受制于第三国,仅表示如清政府将来提出和谈,日本希望其提议尽量由美国公使转达,(68)美国政府居然对日本的答复“表示满意”。(69)19、20日,葛礼山将日本的回复分别通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中国驻美公使杨儒。田贝20日下午向总理衙门通报结果,宣布:“我的政府通知我说,日本可以考虑中国通过我向它直接提出的和平条件。”同时声明“我只要作一个中间人……日本既然不希望斡旋,而是要考虑中国‘直接’提出的条件,所以我预备把中国的提案用密码送达驻东京的美国公使,再由他转送给日本政府。”(70)11月22日,总理衙门照会田贝,正式委托他调处中日战事,称:“贵大臣既有说合之权,应请将中日两国主见互为传述商定,以期早息兵争,仍归和好,庶不负贵国国家及贵大臣美意。”(71)在随后的调停过程中,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驻日公使谭恩作为中间人,与日本的配合十分默契,单方面说服中国方面按照日本的要求和条件举行和谈。
根据11月22日总理衙门的照会,田贝同日致电谭恩,转达清政府已授权他直接提议和谈,条件是承认朝鲜独立和赔偿适当军费。(72)但清政府提出的这一和谈条件遭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26日谭恩代表日本政府复电,指责清政府并没有显现出答应一个令人满意的和平条件的意向,表示如果中国渴望和平并为此任命合适的全权谈判代表,日本将在两国代表会议时提出同意停战的条件。(73)田贝则单方面敦促清政府尽快响应日本要求,选派和谈全权代表,指出日本没有提出媾和的确切条件,这对中国更有利,某种程度可摆脱和谈条件的束缚,并为清政府拟定复电内容。(74)他对清政府内部因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迟迟不对选派和谈全权代表一事作出答复极为不满。(75)清政府12月12日答复,表示愿意根据日本的意愿,任命全权谈判大臣与日本全权代表举行和谈,并建议将上海作为会谈地点。之后,日本方面由谭恩复电,拒绝将上海作为会谈地点和拒绝停战,坚持会谈必须在日本境内进行,并单方面要求中方事先将全权谈判代表的姓名和品级通知日本而拒绝将日本全权代表的姓名和品级事先通知中方。对于日方的无理做法,田贝虽然私下表示有点过分,认为日本故意伤害中国的自尊与面子,(76)但他仍劝说清政府按照日本的要求行事。12月19日、27日,田贝两度前往总理衙门,向总理衙门官员讲解一些国际法基本知识,以欧洲以前签订的条约为例,指出选择和谈地点,是战胜国的权利,并非对清政府的羞辱,敦促清政府尽快选派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和谈,(77)并建议张荫桓最好带上翻译,如有可能,再聘请一名外国法律顾问。(78)1895年1月1日,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在与清朝驻美公使杨儒的会谈中也敦促清政府尽快派全权代表前往日本和谈,指出:“清国如愿与日本帝国进行和平谈判,应派出特派大使着手谈判为妥。如求助于他国则徒失时机。”(79)
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的穿针引线下,清政府的和谈代表张荫桓和邵友濂一行于1895年1月28日抵达日本长崎,30日乘英国“皇后”号邮船抵达神户,再由日本安排的轮船转送广岛举行和谈。但在2月1日第一次会议上,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便对清朝谈判代表张和邵的委任状提出质疑,认为不具备全权证书条件。在2月2日第二次会议上,伊藤博文发表长篇演说,指责清政府在外交上不讲信用,宣布取消和谈。(80)2月4日,日本即安排轮船将清朝和谈使团送回长崎。尽管清政府方面致函日本,表示愿意根据日本的要求,更换委任状,希望日本接受张、邵为谈判代表继续和谈,但日本2月9日由谭恩致电田贝,再下逐客令,声称日本政府绝对不允许中国全权代表逗留日本,他们必须立即返回中国。(81)无奈之下,张、邵使团只好乘法国邮船“威尔奈斯特·西蒙斯”号离开日本回国。
对于日本借口张荫桓和邵友濂不具备全权代表资格,取消和谈,并剥夺张、邵外交和谈之特权,令他们限日离开日本的行为,美国完全站在日本一边,将责任归咎清政府,甚至指责清政府缺乏和谈诚意。充当中日和谈联络人的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在2月4日日方向他通报情况时,明确表态:“日本之措施正当,无可非议。”(82)田贝则抱怨总理衙门颁发的委任状没有采用他拟订的英文本,完全缺乏全权证书的条件,并指责清政府缺乏和谈意愿,幻想通过外国列强的干涉挽救自己,说:“如果中国现在知道世界并不站在她的一边,随她自己开战,那么她将会立即议和。”(83)美国国务卿在日本驻美公使栗野向他通报这一结果时,也对日本的这一决定表示支持,并声称“他已通过美国驻中国的公使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84)
清政府聘请的和谈法律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W. Foster)同样也是为日本服务和效劳。(85)他在12月23日接到总理衙门聘请的密码电报的当日,除拜访葛礼山、征求意见外,还拜访日本驻美公使栗野,通报此事,并保证他本人决不会给日本增添麻烦,做对日本不利的事情,声称:“假若我接受中国差使,将使日本政府感到任何程度的不安,或对我和日本间的友好关系有任何危害的话,我是不愿接受差使而到日本去的。”(86)对栗野向他说明日本此次和谈将会向中国方面提出十分苛刻和严厉的条件,提醒他对此次使命要有充分思想准备,科士达当即赞同日本的立场,承诺将会配合日本说服清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称:“日本政府尔来所采取之措施素为至当。军国之机运将从此而出,乃势所难免,此示为本人所充分了解者。故本人对清国之境域,予以相当之忠告,并使日本政府满意而肯诺媾和。”(87)因此,当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政府通报科士达将以私人身份担任清政府和谈顾问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改变了最初的反对态度,(88)表示很高兴科士达担任清朝和谈全权代表的顾问。(89)
科士达1895年1月21日先期抵达日本后,除收受清政府的聘金之外,(90)果然没有让日本失望,未为清朝谈判代表提供任何帮助。对于2月2日日本方面以清朝谈判代表委任状缺乏全权资格为由破坏和谈,科士达完全站在日本一边,替日本说话。日本取消会谈的第二天上午,日本外务省外交顾问、美国人端迪臣(H. W. Denison)即向科士达说明,日本拒绝和谈的真实原因是认为清朝任命的二位和谈代表官阶不够高,希望清政府改派恭亲王或李鸿章这样的谈判使臣。(91)科士达本人还认为日本拒绝和谈的另一个没有言明的原因是,日本更希望待威海卫战役彻底摧毁和捕获清朝的北洋舰队之后,取得更为有利的和谈条件,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端迪臣的拜访所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对于他们拒绝中国代表并不完全觉得安心,希望通过我向世界更完美地说明他们行动的正常。端迪臣没有说出他们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击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92)然而,科士达这位拿着清政府高额佣金的法律顾问不但没有揭露日本拒绝和谈的真实原因,反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清政府所颁委任状缺乏全权性质这个连日本自己都觉得“并不完全安心”的理由上。在临离开日本之前,他居然对清朝使节的所谓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宣称:“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93)
从上所述,美国这种一边倒的单独调停,除了为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转达信息外,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科士达以私人身份,对清朝政府都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在许多方面帮了日本政府的忙,缓解了日本来自欧洲国家联合调解的压力,为日本继续按计划发动战争、实现侵略要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背景。这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再次得到体现。
四、美国与《马关条约》谈判
日本破坏广岛和谈的目的是为寻找一个日本满意的谈判代表及与中国签订和约的最佳时机。根据近代国际法原理和外交惯例,战争中战胜国的成果只有通过签订条约才能获得合法化。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并俘获北洋舰队全部之余舰,日本政府认为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当天经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清政府转达和谈条件,电称:“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地土及与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以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
收到日本的和谈条件之后,求和心切的清朝政府于2月23日即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致电谭恩,表示愿意和谈,并迎合日本的意图,改任李鸿章为和谈全权大臣,并询问日方:“拟在何处会议,即行复电,以便约期前往。”(9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清朝政府当时虽然求和心切,但对日本提出割地的和谈条件还是持很大保留态度,清廷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主战派坚决反对将割地作为谈判条件,即使是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开始时也不愿意承担割地的千古骂名,奏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95)同时,他拜访英、法、德、俄等驻华使臣,请求这些国家出面干涉,逼迫日本放弃割地要求,希望自己能“在不应允割让土地的条件下前往日本和谈”。(96)在清朝政府和李鸿章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割地的谈判条件问题上,作为调停者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又单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2月22日下午,李鸿章在觐见光绪皇帝之后即拜见田贝,请求美国向中国提供帮助,说服日本结束战争,尤其希望日本方面不要将割让领土作为和谈的条件。对此,田贝明确加以拒绝,警告李鸿章必须首先接受日本方面17日提出的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和割让土地的条件。(97)对于李鸿章向欧洲国家寻求外交支持,田贝极为反感,认为李鸿章的想法不切实际,声称:“在日本的观点公开之前,就国际法来说,任何的干涉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以自我保护为理由。”他强烈敦促李鸿章和清朝政府彻底放弃求助其他欧洲国家干涉的念头,真诚面对日本,指出:“外国的干涉对中国没有好处,它比日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更有可能导致瓜分,除非俄国、英国、法国表现得比历史上更为无私,否则,他们都会为向中国提供服务而要求巨大的补偿。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与日本恢复真诚、友好的邦交关系;日本对中日这两个东方大国从长远角度来看有着共同利益的说法不会不予认同。”同时,田贝还劝说其他国家的公使与他一致行动,打消李鸿章寻求其他国家干涉的念头。他在2月26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在与同僚交谈时,我总是要求他们至少暂时停止讨论有关干涉问题,相反应肯定地表示他们的政府将不会干涉任何不可信的事情,就像我在谈到我的政府时所说的那样。我反复告诉同僚,如果不是因为存在将向中国提供帮助的幻象,我两个月前就促成了和平;只要中国认为,英国或者俄国的枪炮在关键时刻会转而对准日本的船只,它就会拖延直接行动。”(98)
说服李鸿章接受日本割地的和谈条件之后,3月3日下午田贝又在李鸿章动身前往日本前夕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提醒李鸿章和清政府要为支付巨额赔款做好准备,建议李鸿章在离开之前将这个问题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呈明,并有必要向他们提出筹措赔款的办法。田贝向李鸿章授意说:如此巨额的战争赔款,中国不可能通过通常的税收解决,将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到人民身上会产生叛乱;中国为偿还巨额赔款应开发资源,通过修建铁路、开办银行和采矿等实业活动获得财政来源,并要由他本人出使回来后控制和领导这些实业活动,而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和措施还都应掌握在会说英语的人的手里,美国可以为中国提供这样的人才。根据田贝的授意,李鸿章单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转达了田贝这番提醒和建议。(99)
3月19日中日马关条约谈判开始后,清政府继续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降低侵略要求。3月22日,总理衙门除召见俄、法、德、英四国驻华公使外,也召见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征询意见,希望能获得美国的支持,促使日本放弃一些苛刻条件。但田贝不但没有为中国说话,反而责问清政府,指出中国如真想和平,就应该接受日本的条件。(100)
在拒绝向中国提供支持的同时,美国还在国际上帮助日本,抵制欧洲国家的联合干涉。马关条约谈判开始后,为对付俄、法、德、英四国的干涉,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3月19日就电示驻美国公使栗野,请求美国国务卿向驻上述四国的美国公使发出指示,帮助探询四国的意向。(101)对于日本外务大臣的这一请求,美国政府虽然以上述四国很难接近,并以此一做法将惹起其他国家猜疑,使美国陷于困难之地,婉言拒绝,但国务卿向日本公使明确保证“美国决不与上述各国结盟,或接受清国之请求”,并对俄国干涉中日和谈持警惕态度,指出:“俄国并非怀有好意偏向于日清两国之一方,而是急切想抓住一切可利用之机会,以期达到自己目的。”(102)婉拒帮助日本探询各国动向不久,美国国务卿便于3月23日将美驻俄公使了解到的俄国动向透露给日本驻美公使栗野,通报俄国欲占领中国之北部和满洲,对日本占领上述土地及对朝鲜具有保护权持有异议,已派3万军队驻扎中俄边境,有意干涉中日两国间的纠纷。(103)据栗野所说,美国国务卿向他透露俄国这一动向,实际上是对3月19日日本请求美国帮助的一个回应。栗野在3月28日写给陆奥宗光的信函中这样说道:“美国国务卿虽然一度公开表示谢绝,但不数日自美国驻俄公使发来急报。据本官所察,此急报完全是国务卿秘密发出指示,令其复电之结果。”(104)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签订和约,中国国内举国反对;国际上,俄、法、德三国亦以日本割让中国辽东半岛,损害自身利益,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在此形势之下,清朝政府希望推迟交换和约,挽回部分利权。对此,美国的立场再次站到日本一边。4月23日,日本政府召见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委托他求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代为说项,催促清政府尽快批准交换和约,表示:“俟和约批准交换完毕后,我皇帝陛下将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表扬谭与田贝二氏对于和平结局给予之帮助。”(105)4月25日,田贝即致函总理衙门,转达日本的要求。(106)4月27日,田贝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询问“所有与日本商定和约正本可于何日批准”,要求“望即示复,以便电复日本”。(107)
此外,清政府聘请的美国顾问科士达4月22日亦专门致函总理衙门,劝说清政府不要过于计较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说马关条约是清政府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较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结果要好得多。他说:
日本所索之款虽极奢巨,然与普法之役已迥不相侔。查法国所让两省之地,较之奉天南边并台湾全岛为尤要;所赔兵费用金申算,则六倍日本之数。中国地大物博,土肥矿多,户口之繁甲于天下,百姓极为勤俭,工商废而未举,诚能变革中国旧俗,采用泰西新法,富强之期可立而待。不但中日条约让地赔款未足为中国累,而十年之后诸务繁兴,国富民强之效,必为中国前此所未有。区区日本,此约何足深较。(108)
4月30日他又亲至总理衙门,与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庆亲王等会谈,劝说“约宜批准”,(109)声称:“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110)
同时,日本政府还令驻美公使栗野,请求美国政府敦促清政府批准互换条约,对俄、法、德等国的干涉加以牵制,说服三国放弃干涉政策,指出:“日本国政府惟恐俄、法、德三国之活动,将诱使清国抛弃条约,以致再开战端。如此结果需要尽力避免,日本国政府切望美国予以友好援助”;(111)“合众国如能尽力将其从来为和平所施行之调解,施行于上述各国、特别是俄国,以促请对其所提异议进行重新考虑时,本事件将可圆满解决。因此,帝国政府将秘密致函该国政府,表示希望美国给以援助之意。”
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栗野于26、27日两次拜见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寻求美国帮助。在会谈中,对于日本希望美国出面阻止俄、法、德等欧洲国家干涉中日《马关条约》,葛礼山表示“难以对他国活动置喙”,但同时表示美国“始终在为贵国尽力,将竭尽所能给以援助”。对于日本方面请求美国帮助敦促清朝政府尽快批准互换条约,葛礼山则欣然应允,称:“美国政府业于和平谈判开始之际,已给田贝以详细训令,现今政府无须重新去电,谅田贝正在尽力奔走。当然,如有须仔细商议之事,亦可再去指令,决不拖延。”次日,葛礼山即为此专门召见清朝驻美公使杨儒,指出:“日本之要求当与不当,本官虽难以说明,但请清国对今日之状况加以重新考虑。如清国因有足以挽回今日处境之良策,而特意拖延和平条约之批准,日本则将从事更大规模之战争。此时,欧洲各国终将乘机纠缠于两国之间,努力满足其各自欲望。其结果,清国终将不止于失掉辽东,犹恐失去较此更为广大之领土。”(112)与杨儒会谈之后,葛礼山不但将会谈过程告诉日本公使栗野,同时也致电驻华公使田贝,指示他敦促清政府尽快批准和交换条约。(113)
正因葛礼山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态度,日本在5月1日任命伊东巳代治为换约大臣前往中国的当日致电栗野,再次请求美国政府提供帮助,电云:“阁下可会见国务卿,就清国批准条约一事,询问该国务卿自驻清国之美国公使得到如何答复。为批准交换,我国使节已向芝罘出发。故阁下须委托该国务卿劝告清国政府,希清国政府亦派其使节携带批准书前来该地。”(114)次日,日本政府又致函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托其尽速电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按时交换和约。(115)在美国的穿针引线下,5月3日清政府最后任命伍廷芳和联芳为换约大臣,前往烟台。5月9日,正式完成与日本的互换和约工作。
中日批准交换和约之后,由于台湾人民对割台众情激愤,李鸿章和清朝政府希望与日本重新商议台湾问题,但清政府聘请的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又为日本说项,敦促李鸿章和清政府尽快履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指出:“中国有责任向前走下去,忠实地执行条约。”5月18日,接到日本伊藤博文拒绝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议的答复后,科士达即致电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执行条约中关于移交台湾的规定,不要显出犹豫不决或企图逃避。”(116)5月30日,科士达还应李鸿章的请求,亲自陪同李经方赴台完成与日本的交割工作。并且,科士达这次果然充分发挥了法律顾问的作用。鉴于台湾人民武力反抗日本占领台湾,交割工作无法在台湾本岛完成,为按时完成交割工作,避免无限期延迟,科士达想出一个变通办法,让李经方不用上岸便可完成交割工作,指出:“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一个所有权人把大的财产及大块土地移交给另一所有权人时,用一个书面文件叫做‘让渡证书’就够了,把这文件签字,交付后,所有权也就移交了,不需要再去巡视土地。”(117)6月2日,李经方完全根据科士达的建议,与日本桦山提督乘德国商轮“公义”号在台湾基隆海面完成台湾的交割工作。
对于科士达在充当清朝谈判法律顾问期间所提供的帮助,日本政府极为赞赏。日本内阁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在烟台与中方代表完成互换条约后,即向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报告说:“科士达身为对方顾问,非常尽力。天津、烟台之美国领事李德亦给予我方以极大方便。而且由于李德系科士达亲戚之故,又得以间接利用科士达。”(118)1895年6月科士达回国途经日本东京时,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专门通过美国驻日公使邀科士达见面,对他所做工作表示感谢。科士达本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会晤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知道我到北京去并和军机处会议的事情。他对于我努力使条约获得忠实的履行深表赞许。”(119)而对于中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日本天皇在中日互换和约的第4天,也即5月12日,专程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美国国务卿,希望对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予以嘉奖。这一建议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之后,日本又于11月1日将这封感谢信通过日本驻美公使送达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向他表示“最崇高的问候和敬意”。日本天皇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我尊敬的友好的朋友,在日本帝国与中国进行战争期间,在您的善意允许及直接英明的指示下,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和领事官们为我们在中国的日本臣民提供了友好服务,并在许多场合向他们提供援助和帮助。此外,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东京和北京的美国外交代表在您的授权下,为中国能够与我们的政府进行直接联系提供了途径。正是通过在东京和北京的美国外交代表为日中两国政府所提供的直接交流,所有有望最终结束敌对状态的和谈准备工作才得以安排。藉此机会,我们谨对您及阁下的官员们所做的事情表示万分感激。您们所做的工作不仅减缓了战争的残酷和痛苦,并最终成功促成和谈,而且也有助于密切我们两国的友谊和睦邻友好关系。(120)
由此可见,日本方面是多么感激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所提供的外交支持和帮助。
五、美国政府态度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表面奉行中立政策,实际却站在日本一边。它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的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在甲午战争中偏袒日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希望通过日本之手彻底废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发展与朝鲜的关系上,美国始终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看作美国向东亚扩张的阻力和障碍。1882年,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在与李鸿章商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中,就拒绝将有关中朝宗藩关系内容写入条约内。(121)次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 Young)在与李鸿章的会谈中,也反对中国继续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尽管李鸿章向他解释,在中朝宗藩关系中,朝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是自主的,中国并不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朝鲜只是通过一套特定的仪式表达对中国皇帝的忠诚,但杨约翰还是要求中国放弃这种关系,表示中朝宗藩关系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时代错误。截至1886年,朝鲜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签订条约,欧洲列强都继续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或由他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同时负责朝鲜事务。而美国出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反感,则派了一位与驻华公使同等级别的驻朝公使。(122)总之,进入1880年代之后,在判断是朝鲜独立还是保留中国宗主权两者之间哪一种情况最符合美国利益问题上,当时的美国政府诚如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显然倾向朝鲜独立,认为:“在中国庇荫下的朝鲜,料定会拒阻而不会鼓励对外贸易和内政改革……至于既没有保护又没有防备的一种理论上的独立情况可能比维持中国宗主权更坏一节,美国政府似乎始终没有想到。”(123)甲午战争爆发后,10月31日当恭亲王等总理衙门大臣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充当调解人、寻求停战时,田贝公开对清政府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表达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中日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将清政府答应书面同意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作为他同意调停的条件。(124)
同时,美国希望通过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获得了开放通商口岸、传教、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但中国大门并没有完全洞开,清朝政府还没有允许外国完全自由贸易,也没有允许列强在华进行投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日本之手,进一步削弱清朝政府,为美国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扫除障碍。1894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中就反对接受清政府的和谈请求,明确表示在中国军队被日本逐出朝鲜之后即结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应让战争继续进行,要使清朝帝国能够与这个世界和平、融洽,非武力不行。中国遭到败北,直到其皇朝受到威胁,都是有益的事。只有这样的时机到来之际,才是外国进行干涉之时。(125)为实现在中国开矿、修建铁路等投资活动,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的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和美国商人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甚至直接运动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美国驻日参赞史蒂芬斯(D. W. Stevens)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等人,鼓动日本政府攻占北京,推翻清朝政府,日、美联手拥戴李鸿章为中国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妨碍中国市场的发展,阻止修建铁路,允许欧洲人控制中国,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影响力。(126)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田贝在4月29日写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一再抱怨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只追求自身利益,在帮助欧美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投资方面做得不够,背弃承诺,再次暴露了他们当初怂恿日本发动对中国战争的目的。(127)当时美国国内舆论也公开表示,希望借日本之手,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指出中日战争“一旦结束,东方贸易对于美国将具有日益增长的重大意义”;一旦“辽阔的中国领土处在日本的英明管理之下,商业及其他利益……比之任何协定都将增加多得多”,令“美国人对在华商务的真实情况将大开眼界”。(128)此外,美国人认为中国被日本打败还可为扩大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提供方便。《世界传教评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就曾欢呼中国战败的结局“为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开辟了一条捷径”。(129)
其次,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倒向日本一边也是此前美国东亚政策的继续和体现,利用日本以削弱英国、俄国等列强在东亚的影响力。19世纪初以来,美国的亚洲政策建立在使用武力和与其他大国合作这两个原则基础上,但在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在东亚的崛起,美国的东亚政策在1870年代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抛弃欧洲伙伴,单独奉行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削弱英国等欧洲国家在东亚的影响,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130)为此,美国不顾欧洲国家的反对和不满,1878年与日本签订一项条约允许日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1880年代,美国再次不顾英国反对,表示有意在日本取消治外法权。(131)总之,19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正如美国学者所说,“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132)因此,当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升级以后,美国一再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对于甲午战争期间英、美在东亚的矛盾和竞争,法国驻英大使就曾分析说:“英国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角色和他们与日本的关系的担心并不亚于英国对俄国政策的担心。”(133)
同样,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走上向太平洋扩张的道路之后,也开始将俄国列为它在东亚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1891年俄国宣布开始兴建从莫斯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更加使得美国、英国这些试图扩大在华势力的国家神经紧张,倾向利用日本抵制俄国势力南下,认为“只有日本,这个对登上大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国家,才有可能企图在陆上对俄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这一恶梦般的前景进行对抗”。(134)据苏联学者研究,至1890年代初,美国在中国满洲市场上就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在主要商品输入方面将其他竞争者抛在后面。例如1891-1892年,美国输入满洲的主要纺织品品种就比英国多9倍,美国输入满洲的煤油比俄国多1.5倍。(135)因此,为抵制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美国国务卿在调停中日战争过程中就曾劝说清政府放弃亲俄的外交政策,提醒清政府俄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建议中国实行亲日政策,指出:“清国暗中委托欧洲诸国、尤其俄国,使其对日清间之谈判进行干涉,借以削减日本之要求。依据本官之浅见,俄国并非得以作为清国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国家。清国可惧怕之国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国。”(136)同时,美国国务卿也一再建议日本警惕俄国的野心,不要与俄国进行交易,指出:“如日本与俄国达成协议,虽当前无何危害,但俄国野心甚大,令人难以相信。”(137)在以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中,俄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长期以来都是美国防备和遏制的主要对象之一。
事实上,对于美国当时利用日本来实现东亚政策,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同感。如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Gérard)在向法国外长汇报时指出:日本有妄想自己在中国担任文明的传布者、并把欧洲人从这个巨大的帝国中排挤出去的野心;美国赞同日本这些野心的倾向对法国来说非常危险。(138)法国驻英大使顾随(de Courcel)也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Kimberley)警告:当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国家联合行动时,如果听任事态发展,英、法、俄三个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极有可能遇到完全追逐商业利益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今后无疑也包括日本方面的有力的竞争。(139)德国驻法大使敏斯特(Münster)在与法国外长讨论甲午战后东亚形势时亦表示:“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影响是危险的,欧洲应该为她的商业利益担忧。”(140)德国外交大臣马莎尔(Marschall)在与法国驻德大使的交谈中则讽刺甲午战争期间美国人“对日本有一种炽热的感情”。(141)总之,美国奉行亲日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竞争和矛盾。
再者,美国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倾向日本一边亦是受国内舆论和偏见的影响。中日冲突开始后,美国国内舆论普遍同情和支持日本。当日本在平壤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波士顿邮报》就为此欢呼。美国舆论甚至还接受日本方面的宣传,将中日战争看作现代文明与中国保守主义之间的战争,看作是“进步”和“停滞”之间的战争,因此,美国报刊的社论和文章都认为这是像中国这样的保守国家罪有应得的。《世界传教评论》杂志上的一篇社论就挖苦道:“中国这个充满自大的约有3亿人口的天朝帝国一再败在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小国日本手中,谁都不会同情天朝帝国所遭受的耻辱,中国只有自己表示感谢。”激进的共和党人报纸《纽约新闻报》则极力反对美国政府调停中日战争,主张让中国彻底战败,让清朝统治崩溃,指出:“调停的建议是不合理的,它除了符合英国的利益之外,其结果只能使那个可恶、残忍、反动的清朝政府免于毁灭;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因此,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从日本人手中拯救中国是一个有悖国际正义的行为。”(142)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也认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打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如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柔克义就声称:“一次痛击一点也不会伤害中国,它仅仅是一付适合中国的补药。”(143)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则表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对中国所做的,正是美国对日本曾经做过的事情,日本已经学会西方文明,现在正迫使它难以操纵的邻居接受西方文明,中国在世界上的惟一希望是真心地吸取教训”。(144)出于同样的偏见,在中美关于日本间谍案的交涉中,美国的舆论和政客们也多偏袒日本,反对国务卿允许将日本间谍移交清政府,声称这完全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也不只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中国这个半开化的国家不能与日本一样,她无权处理和报复美国的被保护人;向中国移交日本间谍是美国的一个羞辱,它玷污了美国的荣誉、独立和权利。(145)为平息国内舆论和日本方面的不满,葛礼山下达将上海租界的两名日本间谍移交清政府的指示之后,不得不致函清朝驻美公使杨儒,要求清政府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回到北京之前保证不得随便处置。(146)
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的亲日政策,虽然没有直接侵害中国,但无疑为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外交支持,违背了美国声称的对华友好政策。事实上,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始终将美国看作最友善的国家而充分加以利用。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美国希望利用日本来实现其东亚政策,并不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
注释:
①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学者曾对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亲日立场做过比较多的揭露和批判,详见尚钺《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影响和教训》和司绶延《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帮助日本对中朝两国的侵略罪行》(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第85-116页),以及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6-45页)、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90-218页)。但受当时学术环境和资料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著在重建史实方面多有不足。20世纪80年代之后,戚其章教授的《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部权威著作,书中内容多处涉及美国与甲午战争的关系。但由于此著系综合研究甲午战争的国际关系,并把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也未能对美国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述。此外,美国学者魁特(Payson J. Treat)著《美日外交关系史》第2卷(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853-1895)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书中利用了许多宝贵的美国外交档案资料,但作者的学术观点明显亲日,多有偏见,不足为训。
②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3, p.24.
③"John M. S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8, 1894, "in Spencer J. Palmer, e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Far Eastern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 The Period of Growing Influence, 1887-189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331-332.
④"John M. S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9, 1894, "op. cit., p.336.
⑤"Dun to Gresham, June 15,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se Inc., 1981, pp. 87-89.
⑥"Dun to Gresham, July 3, 1894, "op. cit., p.148.
⑦"Dun to Gresham, July 10, 1894, "op. cit., p.154.
⑧"Dun to Gresham, July 14, 1894, "op. cit., pp. 175-182.
⑨"Mr. Denby to Mr. Gresham, June 9, 1894, "op. cit., p.81.
⑩"Mr. Denby to Mr. Gresham, July 3, 1894," op. cit., p. 147.
(11)"Mr. Denby to Mr. Gresham, June 26, 1894, "op. cit., pp. 113-114.
(12)"Mr. Uhl to Mr. Sill, June 22, 1894, "op. cit., p.96.
(13)"Mr. Gresham to Mr. Dun, June 29, 1894, "op. cit., p.142.
(14)《美国公使谭恩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4年7月9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8页。
(15)《朝鲜统理交涉通商事务督办赵秉稷致西露公使》(1894年6月24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430页。
(16)《朝鲜办理公使Ye Sung Soo致格莱锡函》(1894年7月5日发),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36-437页。
(17)"Mr. Gresham to Mr. Bayard, July 20,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 187.
(18)陆奥宗光撰:《蹇蹇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155页。
(19)"Mr. Gresham to Mr. Bayard, July 20,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5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187-188.
(20)"Mr. Gresham to Mr. Bayard, July 20, 1894, "op. cit., p. 188.
(21)"Mr. Dun to Mr. Gresham, June 29, "op. cit., p. 142.
(22)"Mr. Gresham to Mr. Bayard, July 20, 1894, "op.cit., p. 187.
(23)《陆奥外务大臣致驻中国小村临时代理公使函》(1894年7月13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399-400页。
(24)《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3376页。
(25)《总署收驻日本大臣汪凤藻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857页。
(26)《总署发美国公使田贝照会》(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357页。《总署致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60页。
(27)《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386页。
(28)《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18页;《总署致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六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70页。
(29)《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32页。
(30)《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49页。
(3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五日)附录一:《照录美国李领事来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46页。
(32)《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五日)附录二:《津海关道盛宣怀复美国李领事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46-3547页。
(33)《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67页。按:后据石川交代,他确系在中国多年的日本间谍。9月20日清朝按照公法击毙了石川。
(34)《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75页;《总署收南洋大臣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2页。
(35)《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78页。
(36)《总署致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3-1884页。
(37)《总署收驻美大臣杨儒电》(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3页。
(38)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p.484.
(39)《总署收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94页;《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5页。
(40)《总署收驻美大臣杨儒电》(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6页。
(41)《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06页。
(42)《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22页;《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8页。
(43)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pp. 484-485.
(44)《驻美使馆收美国外部葛礼山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90页。"Mr. Gresham to Mr. Denby,August 29,1894,"in 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227-228.
(45)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p. 485.
(46)《总署收驻美大臣杨儒电》(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86页。
(47)《总署致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93、1892页。
(48)《总署收美署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二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894页。
(49)《总署收南洋大臣刘坤一文》(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及附件一:《福原林平口供》、附件二:《楠内友次郎口供》、附件三:《福原林平口供》、附件四:《清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26-3849页。
(50)《总署收浙江巡抚廖寿丰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附件一:《藤岛武彦供词》、附件二:《高见武夫供词》,《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694-3697页。
(51)《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35页。
(52)《总署发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39页。
(53)《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57页。
(54)《总署收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658页。按:对川烟丈之助的在华间谍活动,日本黒竜会编:《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巻(東京:原書房,1966年)中有具体记述,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第232页。
(55)"Mr. Denby to Mr. Gresham, October 31,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274-277.
(56)"Mr. Denby to Mr. Gresham, November 3, 1894, "op. cit., p.298.
(57)"Mr. Goschen to Mr. Gresham, October 6, 1894, "op. cit, p. 252.
(58)"Mr. Gresham to Mr. Goschen, October 12, 1894, "op. cit., p. 252.
(59)《歌坤致格莱锡》(1894年10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47页。
(60)《格莱锡致田贝》(1894年11月24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57页。
(61)《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4年10月21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40页。
(62)M. Patentre,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Washington,à M. Hanotaux,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Washington,8 novembre,1894,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1871-1914),1ère série(1871-1900),Tome 11(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47),pp. 413-414.按:本文的法文资料均由葛夫平同志提供并翻译成中文。
(63)《林外务次官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4年11月8日发),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45页;"Mr. Gresham to Mr. Dun,November 6,1894,"in 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299.
(64)《格莱锡致田贝》(1894年11月6日发),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51-452页。
(65)"Mr. Denby to Mr. Gresham, November 10,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302-303.
(66)《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4年11月8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46页。
(67)《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4年11月13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51页。
(68)陆奥宗光撰:《蹇蹇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167页。
(69)《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4年11月22日发),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57页。
(70)《田贝致格莱锡》(1894年11月22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55-456页。
(71)《总署致美使田贝照会》(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944页。
(72)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pp. 501-502.
(73)Payson J. Treat,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853-1895,Volume II,p.502;北京美国公使馆钞:《美署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7页。
(74)"Mr. Denby to Mr. Gresham, December 8,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p. 10-14.
(75)"Mr. Denby to Mr. Gresham, December 8, 1894, "op. cit., pp. 14-15.
(76)"Mr. Denby to Mr. Gresham, December 29, 1894, "op. cit., p. 60.
(77)"Mr. Denby to Mr. Gresham, December 20, 1894, "op. cit., pp. 29-38.
(78)"Mr. Denby to Mr. Gresham, December 29, 1894, "op. cit., pp. 63-64.
(79)《驻美国公使栗野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1月4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61页。
(80)《有关拒绝张荫桓一行讲和使节经过之奏章》(1895年2月3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86-287页。
(81)《美国驻日本公使致美国驻中国公使电》(1895年2月9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05页。
(82)《林外务次官致锅岛外务书记官电》(1895年2月4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296页。
(83)"Mr. Denby to Mr. Greham, February 6,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p. 92-96, 99-100.
(84)《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2月3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296页。
(85)按:科士达就聘为中方和谈法律顾问,固然名义上为私人身份,但由于他本人为美国的前国务卿,其担任和谈顾问不但事前得到国务卿的首肯,而且事后也得到美国政府和美国驻华和驻日外交官的密切配合与支持,因此,科士达的使命实际上很难说是纯粹的私人性质,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已代表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86)《科士达回忆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65页。
(87)《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4年12月29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82页。
(88)按: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最初担心科士达作为他的私人朋友担任清政府的谈判顾问,可能于日本不利,曾指示日本驻美公使栗野设法阻止,详见《陆奥外务大臣致驻美公使栗野公使电》(1894年12月26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9册,第480页。
(89)"Mr. Dun to Mr. Greham, January 17,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p. 71-72.
(90)按:清政府聘请科士达为和谈法律顾问的月薪为1万美金,共支付了3万美金,详见《总署收钦差大臣李鸿章电》(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三,第1974页;《总署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文》(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第4373-4374页。
(91)按:在2月2日的会谈中,张荫桓就曾询问伊藤博文拒绝和谈,是否因为他们的官阶不足以充当中国的全权大臣,伊藤予以否定,坚持只是因为张的委任状未授予适当的全权(见戚其章主编:《有关拒绝张荫桓一行讲和使节经过之奏章》(1895年2月3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288页)。日本方面之所以在公开场合不说明此一理由,这是因为清政府早已将谈判代表的姓名和品级通知日本,并得到后者的认可,而日本方面直至和谈的前一天才将他们的谈判代表通知清朝谈判代表。因此,日本如以张、邵的官阶问题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显然会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地位,要为此次和谈失败承担责任。
(92)《科士达回忆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72页。
(93)《日方记载中的中日战史》,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268-269页。
(94)《美署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09-610页。
(95)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页。
(96)"Denby to Gresham, February 26,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 170.
(97)"Denby to Gresham, February 23, 1895," op. cit, pp. 152-154.
(98)"Denby to Gresham, February 26, 1895," op. cit., pp. 159-162.
(99)"Denby to Gresham, March 5, 1895," op. cit., pp. 193-198.
(100)"Denby to Gresham, March 23, 1895," op. cit., p. 231.
(101)《陆奥外务大臣致驻美国栗野公使电》(1895年3月19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69页。
(102)《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3月21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70页。
(103)《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3月24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74页。
(104)《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3月28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76页。
(105)《陆奥外务大臣致林外务次官电》(1895年4月23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49页。
(106)《总署收美使田贝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第4246页。
(107)《总署发美使田贝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第4253页。
(108)《总署收美国科士达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第4244-4245页。
(109)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553页。
(110)《科士达回忆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80-481页。
(111)《陆奥外务大臣致驻美国栗野公使电》(1895年4月26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146页。
(112)《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5月7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180-181页。
(113)《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4月27日)、《陆奥外务大臣致林外务次官电》(1895年4月29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148、351页。
(114)《陆奥外务大臣致驻美国栗野公使函》(1895年5月1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51页。
(115)《陆奥外务大臣致美国公使函》(1895年5月2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351-352页。
(116)《科士达日记》,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628页。
(117)《科士达回忆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85页。
(118)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3页。
(119)《科士达回忆录》,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7册,第486页。
(120)"Emperor Mutsuhito to Grover Cleveland, November 1,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343.
(121)《总署发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光绪八年三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57-565页。
(122)按:当时欧洲国家都承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由派驻北京的外交官负责朝鲜事务。
(123)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85页。
(124)"Mr. Denby to Mr. Gresham, October 31, 1894,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I, pp. 279-281.
(125)"Denby to Gresham, October 23, 1894, "op. cit., pp. 254-259.
(126)有关此一计划的详细情况及过程参见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30.
(127)"Denby to Gresham, April 29,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p. 289-299.
(128)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杨诗浩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13-14页。按:有关19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对扩大对华贸易的憧憬及这种憧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可参见Thomas J. 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1893-1901,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7.
(129)Marilyn Blatt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p.22.
(130)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第387页。
(131)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姚曾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55-361页。
(132)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册,周桂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133)M. de Courcel,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ondres, à M. Hanotaux,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ondres,10 avril,1895,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1871-1914),1ère série(1871-1900),Tome 11,p.726.
(134)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李金秋、姚宝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有关19世纪美、俄两国关系演变更为系统的论述,请参见Edward H. Zabriskie,American-Russian Rivalry in the Far East: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1895-1914,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6.
(135)C. B.戈列里克:《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高鸿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136)《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5月7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181页。
(137)《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1895年4月5日)、《驻美国栗野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函》(1895年4月16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0册,第86、104-105页。
(138)M. de Courcel,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ondres, à M. Hanotaux,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ondres, 5 mars, 189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1871-1914), 1ère série(1871-1900), Tome 11, pp. 602-603.
(139)M. de Courcel,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Londres, à M. Hanotaux,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Londres, 10 avril, 189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1871-1914), 1ère série(1871-1900), Tome 11, p. 675.
(140)Note du Ministre, Paris, 5 avril, 189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1871-1914), 1ère série(1871-1900), Tome 11, p. 661.
(141)M. Herbette,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Berlin, à M. Hanotaux,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Berlin, 18 avril, 189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1871-1914), 1ère série(1871-1900), Tome 11, p. 704.
(142)Marilyn Blatt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pp.21-23.
(143)"William W. Rockhill to Alfred Hippisley, October 30, 1894, "in Rockhill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44)"Denby to Gresham, February 26, 1895, "in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II,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1894-1905, Volume 3, The Sino-Japanese War II, pp. 162-163.
(145)Marilyn Blatt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pp. 25-26.
(146)Payson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853-1895, Volume II, p.487.
《历史研究》2011年2期 作者:崔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