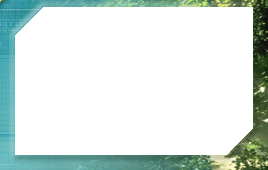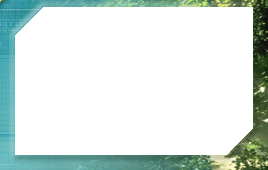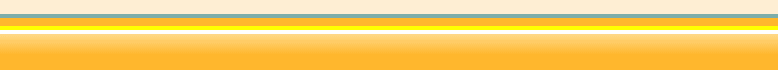(一)
《白鹿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通过文化批评的方法,揭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存在的“《白鹿原》式”的生命文化苦难,表现了民族生命个体生命意识无目的的涌动和盲目的冲撞,直言出一个久经苦难、饱经沧桑的伟大民族试图摆脱一种文化苦难,而最终又不能不归于这种文化苦难的悲凉文化结局。它用了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反映出了一个只有用科学批评方式才能反映得清楚和深刻的文化主题,通过一群“白鹿原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舞台的全面文化突围和全部文化遇难,点明了我们中华民族迁移过程中先天存在的某种文化悲剧性。
“白鹿原人”是一个苦难的社会文化人群体,孤独的社会文化人群体,他们的苦难性、孤独性,不仅在于他们曾为自己的文化命运而战,而抗争,不仅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出路寄予过多的文化观照和文化探询,不仅在于他们的人生和悲剧性是具有某种民族典型性和文化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终生奋斗的文化结果,竟是使他们的人生结局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悲剧一致性。他们都害过人,被人害,杀过人,被人杀,无论是生老病死,死亡成了他们人生的唯一结局和永恒主题。他们要么灵魂和肉体双重死亡(如小蛾、黑娃、鹿子霖、兆鹏媳妇、白灵、鹿三等),要么,活者如同行尸走肉,其实灵魂已经死亡(如白嘉轩、鹿贺氏等)。总之,《白鹿原》人的文化命运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个体命运的最好概括,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范式中最悲壮的艺术史诗。正如叔本华所言:“在人类的苦难中,完全暴露出意志的内部冲突。苦难之来到人间,部分是由于机运和谬误的作用。这种机运和谬误是作为世界的主宰,并人格化为命运而表现出来。①”的确,《白鹿原》中所体现出的全部民族文化悲剧正集中表现为苦难。苦难的命运,苦难的结局。苦难使主人公六娶六丧,使白鹿两姓子子孙孙代代相斗,使白鹿原王旗变幻,翻云覆雨;正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使白鹿原人冤冤相报无止无休;苦难造成了生命文化个体和民族文化集体命运的悲凉,使古老的土地在历史的阵痛中挣扎,使新生的政权在文化的血泊中颤栗。是苦难,使白鹿原人蒙受了太多的社会耻辱;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品尝了太多的生命苦果,历史机运和文化谬误在小小的白鹿原上悄然汇合,它们共同交恶,合谋策划了白鹿原人无法穷尽的人生悲剧。应当说,白鹿原式的民族文化悲剧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悲欢离合、善恶生死,既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对抗所形成的强烈内部文化意志冲突,又是文化弱肉强食、物极必反规律的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约定和文化印证。惟其如此,当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白鹿原》时,都会被其中的主人公近乎历史谶言式的悲剧命运文化结局所惊异,所震慑。我们想弄清楚《白鹿原》悲凉生命个体文化苦难和民族集体文化苦难发生的历史原由,想弄清楚《白鹿原》文化历史梦魇式的文学呓语背后,所掩藏的深层民族文化历史动因,是什么原因,使这部作品让我们领悟并体味到我们现在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苦涩。而且正是这种文化苦涩,它常常令我们无缘无故地叹息,令我们无缘无故地为一群人、一个民族,在广漠的历史岁月中,悲恸不已。
毫无疑问,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小蛾、鹿三等人,是那“一群人、一个民族”的忠实文化艺术代表,在他们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洞悉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又可以观摩造就那个悲剧时代的历史机遇和文化谬误。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文化叙述的艺术解构手段,文化还原的艺术批评方法,达到分析他们、反归他们典型人物形象原本文化面目的终极艺术目的。也许,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揭开《白鹿原》文化苦涩韵味的艺术之谜。
1.文化先知者朱先生
这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艺术人格形象。作为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儒家思想熏陶。他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的一切行为都表明,他修身养性的功夫,已使自己达到一个芸芸众生不可达到的人生境界。他是一位圣人,年轻时择偶标准的与众不同,已显示出他所具有超凡气质,尤其是结婚后他和朱白氏居住在远离人间烟火的白鹿书院,更是为流传在白鹿原上的有关他的 传奇故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他是一位神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普通百姓看来,都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文化魅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动,都被演绎成一个又一个只有在天书中才能读到的离奇故事。他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平日里粗茶淡饭,编县志,做学问,只有在当清兵来犯、乌鸦兵作乱,年馑大饥饿,日寇大入侵时,他才毅然走出书斋,以身明大义之举,爱国爱民爱家的“仁义”之心,赢得了白鹿原人的普遍敬仰。他也是一个智者,具有预测未来的非凡能力,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情世故,能测出农人丢失的牛的走向,能解开“白鹿”传闻的文化秘结。他还能预言出乌鸦兵作乱的最后结局,也能预感到白灵等人的死亡消息……。的确,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神,他的那些充满天玄地机哲理意味的诗句,因为具备了惊人的先天预见力,因而令人听到了心惊肉跳。他说:“房要小,地要少,一头黄牛慢慢搞”,谁知,这近乎谶言的警句,竟不幸而言中了解放后那些家大业大的地主们的必然人生结局。《白鹿原》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朱先生的丧葬观念,在人们崇尚厚葬的社会环境中,他竟留下了死后“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奇怪要求。人们惊讶他这个怪人的怪癖,百思不得其解他这个文化老人的深刻用意,竟以为这位老先生老糊涂了。然而,几十年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才使白鹿原人如梦初醒,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挖开朱老先生的坟墓时,他们惊异了,竟然在其中找不到一丁点值钱的东西,他们找到的唯一的一块有用的砖头竟然是一块阴阳卯合的神奇砖头,上边赫然写道:“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振聋发聩之语,他简直是对不肖后人的莫大嘲讽,白鹿原人的人们终于体会到了朱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他们深深为老人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所折服。毫无疑问,《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一位深谙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规律的文化先知。虽然,从表面上看,《白鹿原》中对他那些非凡才能的描写,具有夸张和渲染的文学色彩。但是,从他这个文学形象身上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内涵来看,笔者仍然认为:那些预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脑海中的无意识历史经验总结、积淀和整合,才培育形成了他和其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异乎寻常的理性文化直觉。使他们能预感到中国社会未来多少年内的大概历史文化走向,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选择自己人生行动。正由于此,我们才说,每当社会动乱之秋,朱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都能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时局,作出一针见血的中肯预言。
再者,《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还是一个道德完人,不知是他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决定他必然会成为一个社会理想文化完人,还是他的社会理想完人特性造就了他的半人半神特性。总之不管怎么说,他的淡泊明志,修身养性,的确使他成为《白鹿原》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伟大象征和不朽化身。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社会理想文化人格艺术形象,才决定他必然会养成身上不着一丝洋线的独特文化生活习惯;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完人特性,才使他在死后,因儿媳没给他穿老伴做的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竟然“两条腿微微打弯而不平展。”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穿上了,朱先生的腿舒展了,这个荒诞不经但的确令人信服的文化细节,也许是作者陈忠实为我们故意编造杜撰出的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但是,为什么是他——朱先生成了这艺术文化神话的主人公,而非别的什么人,笔者认为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是的,是他的关学最后一个大儒身份,决定他必然成为白鹿原人心目中的文化偶像,是他的圣人特性、仁人特性、智者特性、神人特性、完人特性,决定只有他才能成为《白鹿原》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中,唯一的理想文化人格神话对象。白嘉轩说过,“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朱先生的过世,不仅标志着他所代表的那个田园牧歌式的儒家民本传统文化社会的终结,它也说明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崭新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它预兆着,人们将从沉睡已久的亚细亚儒家农耕文明中逐渐觉醒。朱先生走了,他的走,意味着传统理想文化人格形象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的最后缺场退席。从此,中国人将不得不对自己永远丧失了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理想文化人格形态,而陷入永久的文化缺憾、懊丧和无奈当中。文化先知者朱先生走了,他将中国文化和白鹿原人推向了新的文化无知中去了,面对未来,我们不能不忆起朱先生,想起他在《白鹿原》上所说的那些话。也许,我们民族最终能记录他所说的那句至理名言“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违”。
2.文化负重者白嘉轩
白嘉轩是《白鹿原》中的主线人物,他是朱先生那样文化先贤圣哲们的忠实追随者,他一生唯朱先生马首是瞻,唯朱先生言听事从,朱先生所制定的白鹿村《乡约》,只有他忠实执行得近乎迂腐,他一生腰板为何挺得太直,乃是因为朱先生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给他注入了过盛的生命文化底气,他的腰板最后之所以被黑娃打弯,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重荷早已压弯了他的精神脊梁。毫无疑问,白嘉轩这样的白鹿原人是传统文化延续和传播的主要文化载体,他的主体角色文化位置,决定他必然会成为白鹿原这个小小的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文化分子。家庭、祠堂,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信仰的理想文化场所。是朱先生使他“先知”,是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使他“后行”。面对命运,他泰然处之,百折不挠。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由于此,黑娃落难时,他才能鼎力相助,无怨无悔。但是,他又刻薄残忍、冷酷绝伦,因而他面对无辜的小蛾,仇视无比,竟至死后也要将其骨头烧成灰烬压在塔下而后快。是谁给了他那种忠实捍卫封建社会秩序和尊卑观念的勇气、毅力和自信,是谁将他异化成了一个非人的冰冷的邪恶的文化理性怪物,是谁让他错将正气当邪气,反将邪气当正气,是谁支配着他的意志,使他于悲惨的晚年,目睹了白鹿原上一切曾经辉煌过的生命悲惨地死去,是谁让他充当一个沧桑社会的经历者、旁观者、害人者、受害者,然后在一种悲凉的心态中一天天憔悴和衰老下去。我们说:都是因为迂腐、野蛮、残酷的传统文化陋习,使他成为一个连他也不认识的理性政治怪物,由于此,他面对死去的六任妻子,毫无仁爱之心,就象糊窗纸破了揭去再糊一层一样。他满脑子装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千古遗训。巧夺风水地,显示了他的精明;与鹿子霖明争暗斗,显示了他有着惊人的圆滑和世故。他暗藏杀机却含而不露,他内心奸诈却为维护封建家族的宗法名誉,义无反顾。他以一个封建卫道士的身份出现,修祠堂,办学校、教风化、正人伦……。他象一个灭火队员,四处奔跑,妄图扑灭到处燃起的革命叛逆之火;他象一个社会宪兵,整天忙于白鹿原上的道德执法,他就是那个道德检查官。白鹿原上没有人比他活的累,没有人比他活的苦,封建传统文化的重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压抑得他失去了他的“自我”和“本我”。于是,他成了一个超越他人自体本身的家长、族长。于是他身上便具备了一般人不曾具备的文化残忍性格,他对待孝文和白灵不留情面;对待小蛾,残酷得令人发指。他是一切罪恶的主谋,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文化杀手,没有人不慑于他的淫威,没有人不敬仰他的尊严。是啊,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他刚强的文化个性;是封建道德礼教,磨砺出他成熟的传统文化理性人格。然而,传统文化的重荷简直太重了,没有人能负载得起,朱先生那个文化圣哲不能,他更不能。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革命正在熊熊烈火中爆发、燃烧,他所捍卫的那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但是,他中毒太深了,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块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黑娃打弯他的腰不是偶然的,黑娃不打自然会有别人去打,无数“黑娃”组成的庞大的革命者群体,正在一天天打垮着他的传统文化意志和传统文化信仰,就连他心爱的子女白灵也参加了这个革命行列。于是他心灵衰老了,心灵上的衰老加速了他的肉体上的衰老,当他拄着拐杖,匍匐在他所热爱的土地上,回想着他所招致的一个又一个文化惩罚和文化失败,他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命的孤苦和悲凉。孝文的堕落,白灵的出走,赵白氏的瘟疫而死,自己的腰被打折,这一系列事件象过电影一样闪现在他自己的脑际。尤其是当他最后“看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把一颗鲜灵灵的羊奶奶递到他眼前:‘给你吃,给你吃,咱俩好!’”时,他“轻轻摇摇头,转过身时忍不住流下泪来。”他是在为谁而哭,为鹿子霖吗?为所有遭难的亲人吗?为这在不幸中挣扎的白鹿原吗?这其中难道没有他自己,没有他所誓死捍卫的中国传统文化吗?白嘉轩到底为谁哭?作者没有过多的交代,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疑问,一个千古难解的历史疑问,这个问号也许可供我们世世代代思考下去。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白嘉轩的哭,他是在为属于自己的时代和属于自己的文化正在无情地死去而哭。一个新型的革命文化正在崛起,这个革命文化,正在对白嘉轩这样的历史文化老人提出挑战,如果他胆敢继续顽抗,也必然是死路一条。但是白嘉轩毕竟是白嘉轩,传统文化的特性造成了他生命力的旺盛,造成了他矢志不渝的韧性,以黑娃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势力虽然打折了他的腰,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那被传统文化重荷压弯了的生命意志却始终不曾垮掉,他顽强地生活在白鹿原上,虽衰而不老,他还要继续经历和目睹在中国社会以后的历史文化变迁,并且在世纪的风风雨雨中长生不老。白嘉轩形象令我们想起了几千年长生不老、衰而不死、反复循环的中国封建文化,他不正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全部文化象征吗?
(二)
3.文化两面人鹿子霖
与白嘉轩一味继承圣意、实践具有鲜明儒家色彩的处世哲学相反,鹿子霖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认同和审视,选择与实践,则有些半心半意了。理论上,他接受先贤圣训,现实生活中,他却放荡不羁,心猿意马,仅仅将其当作“面子问题”。由此,他以拥有“干儿”最多闻名于白鹿原。他不惜以卑鄙的手段,占有了小蛾,又无耻地利用了小蛾,他施展美人计,眼看着自己的夙敌白嘉轩之子白孝文被拉下水,他终于松了口气,为自己能给白嘉轩的脸面子上泼了一盆屎而得意。然而,社会是无情的,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和白嘉轩斗,结果却还败在白家手中。可是,不管怎么说,鹿子霖也是一个胜利者,他以一个区区乡约官职(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官职),就可以在白鹿原上呼风唤雨,大手一挥,就让他的所有干儿子躲过了兵役;屁股一抬,就可以祸害百姓,令他们家破人亡,这一切,不正说明,鹿子霖所代表的那一种文化力量,也曾在白鹿原上有过辉煌的历史吗?鹿子霖这个传统道德文化的虚伪继承者,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灵与肉,情与欲,真与假,善与恶,这一切,充斥着他的一生,使他一辈子都在理性文化与世俗文化间徘徊,令他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游移。他的处世哲学正是这样始终在正义与邪恶的煎熬和折磨中痛苦地选择。他饱读四书五经,熟识礼仪廉耻,但是却永远在心灵深处,仅将其当作文学游戏和遮羞布。一切的一切,均无法阻挡他不断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罪恶脚步。正因为如此,作为公公,面对兆鹏媳妇,生活中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是,作为男人,心灵中,面对兆鹏媳妇那样的成熟女性,他总不能永远无动于衷。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折磨着他,于是,鹿家大院里,上演了一场公公与儿媳、男人与女人,有关麦草与苜蓿明争暗斗的悲喜剧。老驴还想吃嫩苜蓿,但他始终没敢吃这口嫩苜蓿,这是鹿干霖在传统道德文化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之下,所做的巨大理性妥协和让步,他不得不作出这种妥协和让步,尽管他这头老驴仍有能力吃动那口嫩苜蓿。鹿子霖的悲剧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来自社会强大的道德理性文化,与源于人自体生生不息的生理欲望那种非理性文化。正是二者在他身上有机的交汇,无情地较量,反复地争斗与冲突,造成了他文化人格上的“两面游移”,从而将他真正塑造成一个合现实的文化两面人。并且,随着那两面文化相互斗争的升级,他的内心愈是显得焦灼、痛苦和难忍。于是,悲剧发生了,只有当他的精神完全走向崩溃,他才有可能摆脱传统道德理性文化与现实非理性文化的双重奴役。小说的结局正是这样的,鹿子霖的疯和老年痴呆,暗示他已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意味着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最终获得了精神的彻底解放,尽管这种解放以精神的崩溃为代价。鹿子霖,这个普遍的社会原生人,他终于实现了其独特的文化原生人的文化回归。正由于此,小说最后,鹿子霖才将白鹿原当成了自己精神的伊甸园,他“常常脱得一丝不挂满街乱跑”,“把一颗鲜嫩嫩的羊奶奶递到”白嘉轩“眼前”,“你吃吧,你吃吧,咱俩好”,听完鹿子霖的话,白嘉轩“忍不住流下泪来”。是啊,谁也不能怀疑此刻鹿子霖的真诚,这是一种远离社会文化的自然真诚,这种真诚的确来之不易,它以毁灭鹿子霖的一生来获得,以毁灭生命的理性文化和本体文化为代价,其不可谓不残酷。鹿子霖死了,他是在天明时死的,他是在新时代的文化曙光中死的。他的死表明,一个具有继承传统文化表面特点,而骨子里又具有叛逆传统文化本质内容的“文化两面人”,他处在一个非此即彼、必须作出人生选择的社会里,其死亡和痛苦是命中注定的,其命运必然是悲惨而无望的。一味地屈从、一味地背叛,固然也很可悲,但是,一味地摇摆不定,亵渎传统文化,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灾难。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社会文化又同样玩弄了他,他的两面性无疑是他所处社会文化两面性的写照。从这一点讲,他的形象存在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宜的。但是,从他的人生结果看,他所追求的东西与他最终得到的东西,却是相去甚远的。
4.文化反叛者鹿兆鹏和白灵
如果说前面三个人物形象都是以传统文化卫道士社会角色活动在白鹿原社会舞台上的话(至少在表面),那么,我们要说,鹿兆鹏和白灵则是以传统文化的反叛者角色进入读者的白鹿原人物形象文化视野的。小说文本中,他们之所以走向革命,一是青年人所特有的不满足现状的个性使然,二是新式教育的结果,三是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时代,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必然。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驱使他们必须扮演文化反叛者的社会角色。小说中,走向具有现代文化意味的新式学校,是鹿兆鹏和白灵反叛传统文化的必要步骤,朱先生白鹿书院日渐遭到人们的冷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文化青年普遍远离和扬弃了传统的文化教育。毫无疑问,鹿兆鹏和白灵的反抗之路是艰难的,他们不但要承受强大的封建道德文化、宗法观念、伦理思想等多种社会因素,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而且还不得不反抗祠堂,背叛代表父辈文化的族长、家长。由他们发动组织的农民风搅雪运动,使原本死水一潭的白鹿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革命势头,而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社会时局,也不断推波助澜,使他们的反叛显示出某种特有的时代特征。应当说,《白鹿原》中,前边我们讲过的那三种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圆形人物”,只有鹿兆鹏和白灵他们这些传统文化反叛者,才具有“扁形人物”的全部艺术文化性质,他们二人形象,远没有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那么复杂,他们热情、执着、单纯得就象一张纸、一团雪,他们对革命痴心不改,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作者是寄托了某种政治理想的。而且,文本中,作者借朱先生之口,将白灵比作白鹿,这就等于说,共产主义正是那个令白鹿原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的白鹿,而白灵正是其的美好化身和象征。然而,同样是革命者,旧时代的文化反叛者,白灵和鹿兆鹏最终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白灵死了,她是被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杀害的,她没有死在反叛旧文化的战斗中,却死在新文化的叛逆者手中,革命者死在革命者的刺刀下,这多么令人意外和震惊,但正是这,作者才真正为读者揭示出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白灵的死告诉我们:当一个文化叛逆者并不容易,它有时需要文化叛逆者以生命为抵押,以死亡为代价。它也告诉我们:革命同样不能避免悲剧,而且有时还会制造悲剧,加深悲剧。革命者可以获得反叛旧时代的胜利;但有时却无法获得反叛革命异己分子的成功,面对打着革命旗号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反叛,有时显得是那么地徒劳、天真和可悲。
5.文化变色龙白孝文
白鹿原年轻一代文化人中,白孝文无疑是一个最复杂的人物,这位从小饱受儒家礼仪廉耻教育的青年,他的好学、练达和成熟,曾使他的父亲对他充满希望。尤其是宗族事务的介入,更是使他成为未来白鹿原最有前途的族长和家长形象。但是,也正是这位饱受礼仪廉耻的文化青年,其最后的寡廉鲜耻政治人格,同样也令人吃惊。在鹿子霖的诱使下,田小蛾将他从理想的狂巅拉入非理性的深渊,当他的意志、道德等品质如迷途的羔羊在白鹿原上徘徊的时候,他的肉体也如饿狼一样在白鹿原上流浪,为了满足昼夜难熬的性欲和毒瘾,他竟至抛弃妻子儿女,倾家荡产。结果白鹿原上的沟沟坎坎,成了他生命的栖息地,直到最后,他竟完全沦落成为一个叫花子,不惜混进难民营中,去抢舍饭。白家大公子的堕落与白家大公子当年的威风——这一巨大的现实落差,着实令白鹿原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实在弄不明白,一个人的命运的变化怎么那么地反复无常。当人们将诧异的目光一次一次地指向白孝文这个白家大院的落难公子时,人们这才发现,命运再一次愚弄了人们的眼光。鹿子霖一句话,使白孝文摇身一变,成为县保安队的文秘书手,是鹿子霖扮演了败坏和成就白孝文的萧何角色,给白孝文的人生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机遇 ,这位昔日的浪荡公子,最终成为保安团营长,既买回了从自己手中卖出的院基,又为白家赢得了面子,谁也没有预料到,过去那个败家子,如今成了大事业。白孝文官至滋水县县长时,白鹿原人(包括其父亲白嘉轩)都为之侧目,作为玩弄政治的好手,他象一个文化变色龙一样,一次次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角色,终于成了深谙政治韬晦之术的大阴谋家。正因为此,他才可以摇身一变,由国民党政府的要人变为共产党地方政府的高层人物,他先走一步,向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发致敬信,并且以一个成功的政治投机家、阴谋家的社会面目出现,整死了真正的革命者、与他一起长大的朋友黑娃。白孝文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了他多么富于心计和政治眼光,表明他已具有成熟的卑劣的政治手腕,他终于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走向成功的政客一样的政客文化人形象,一切卑劣的手段和歹毒的心眼,在他身上都显得极为平常,在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中,他一次次高升,面对这样一个残忍而又奸诈的文化变色龙,政治变色龙,人们越发感到社会的诡谲和变幻莫测。应当说,白孝文文化变色龙形象是我国封建传统文化政治社会的产物,他具有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素质,又具有封建政客文化人的共同本质,他的奸诈、残忍,多少能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他炉火纯青地驾驭政治时局的能力,进一步说明,他是白鹿原文化社会一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他不象朱先生、白嘉轩、鹿三那样,扮演了白鹿原封建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角色,而是在白鹿原政治风云变幻史上,能干大事情的文化变色龙的再世。他狡猾而卑劣,善于审时度势,决定了他必然在政治舞台上走向成功;他不露声色,对权力的无穷贪欲和为追求权力而表现出的那种坚韧精神,决定他必然是白鹿原上最具强壮和旺盛政治生命力的政治文化人形象。毫无疑问,在白孝文这个形象上,作者倾注了太多的文学心血。他让白孝文象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白孝文的发迹表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封建思想残余还很难随着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消亡,它必然随新文化存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而,类似白孝文这样的政治变色龙、文化变色龙社会角色,还会得势多时。虽然,作品中,作者并未对白孝文的心理作太多的剖析,但是,通过白孝文文化行为的一系列叙述,作者仍向我们揭示白孝文形象的独特性、代表性、典型性和丰满性。白孝文政治投机行为的成功向善良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政治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谨防这些政治变色龙、文化变色龙,败坏政治,贻害民族,亵渎文化。因为,正是这类角色,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带来过无穷灾难、痛苦和不幸。
(三)
6.文化回归者黑娃
黑娃是一个长工的儿子,他的贫穷和低贱社会地位,决定他的童年必将在大自然的哺育下度过,于是,在他的身上就具有了中国农民广泛具有的土地一样的淳朴、热情、自由和豪爽,也就具有了土地一样的粗犷、倔强、执着和坚定。他聪明、坚韧而富于进取意识,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尽管,白鹿原上还有白嘉轩这样一个仁慈、善良的族长、家长、地主,善待他父亲鹿三,平等地将他和白孝文一块送进学堂,但是,这个封建社会秩序对人本质的不平等,时时吞噬着他痛苦的心,令他深切地体会到一种任人凌辱、寄人篱下的感觉。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安、浮躁和压抑的情绪,社会对之于他,似乎更多的暴露出一种人性的扭曲、分裂和异化。生活无法改变他父亲与白嘉轩仆与主的本质,一种被雇佣的关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长工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当他面对以严厉著称的白嘉轩时,不由得涌起了对这位老人和他所代表的强大封建文化的敬畏和仇恨。正因为这样,他嫌白嘉轩腰挺得太直,特别是当白嘉轩所代表的那个宗法制度、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拒绝并扼杀了他心爱的小蛾时,一种被拒绝和被毁灭的耻辱,深深地刺伤了他年轻的心。于是,这个桀骜不驯的青年反叛者,在这种强烈、沉重的屈辱情绪支配下,开始走向反叛封建宗法社会道德秩序的叛逆之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带领土匪打断了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杆,领导农会砸碎了象征封建宗法社会文化权威的祠堂中的“仁义白鹿村”石碑,“把白嘉轩的这一套玩意收拾干净”,他那颗狂躁不安、难于驾驭的心灵才获得了满足,并且得到了些许慰籍。
但是,无论如何,黑娃所代表的文化反抗力量是盲目的。尽管他参加了农讲所,和农会的同志掀起了白鹿原上的“风搅雪”,接受了国民革命军习旅的血与火的洗礼。然而,他对革命军虽不乏真诚和热情,却总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式的农民习气,他对革命的真诚和热情是建立在农民所特有的小农经济利益上的,这就使他的革命和反叛,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软弱性、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正因为如此,当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之后,他顿时失去了心理依托,他的革命意志也随之涣散和瓦解了。终于,黑娃沦为土匪,直到他的队伍被招安改编成县保安团炮营之后,他的心灵仍然迷失在盲目的低谷中,他不知他人生的出路在那里,更不知男子汉的他,该向那个方向进行文化突围。正是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文化烦恼境地中,他开始了向传统儒家文化的昄依和回归。于是,他用惊人的毅力,让部下把他绑在炮筒上五天五夜,戒了烟瘾,娶回了高老秀才的女儿,成了朱先生的忠诚弟子。他回到了白鹿村,领着媳妇叩拜了父亲鹿三和族长白嘉轩,并且戏剧性地跪在被他砸碎的祠堂“仁义白鹿村”牌匾前。这是历史对黑娃的无情嘲弄,也是历史对革命的无情讥讽,更是历史对五四以后新文化的羞辱。黑娃跪倒在祖宗牌位前,祈求祖宗对他的革命罪孽进行宽恕,正如白嘉轩所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黑娃也不例外,当他跪倒在祠堂里时,标志着他人生开始了又一轮回的否定,不过这次否定比他以前的否定,更具彻底性和反动性。黑娃的文化倒退说明,即使再强大的人群,一旦他们的心灵中没有先进和科学的理论做灵魂支柱和理论指导,他们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们所反叛的文化力量所征服,并且再次被逼迫沦为传统落后文化所奴役的精神奴隶。正由于此,黑娃向朱先生的拜师,成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回归者的“回归”顶峰,当他注视着朱先生为他题写了“学为好人”的条幅时,这就预示着他将成为朱先生所代表的那种仁义儒文化的“最后一位弟子”。“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去闯世事,你是过了世事才来趸学问;别人是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朱先生对黑娃的感慨不是偶然的,他说明,黑娃所代表的被压迫力量对精神文化的渴求是真诚的、坚韧的,尽管他的追求有时候有些愚昧和盲目,并且经常被落后的文化所蒙蔽。然而,正因为他对精神文化的不懈追求,才促成他会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由于没有科学的先进的价值文化所引导,这就注定他在人生的旅途中找不到正确的坐标和归宿,正因为这样,他的文化突围才不可能成功,他的革命才会中途夭折,他才会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出路。黑娃的文化精神被打垮了,打垮他的不是他自己,是由于封建文化力量的强大和其强大的同化性。正因为这样,与其说是黑娃自觉自愿地扮演了一个白鹿原上的“文化回归者”形象,毋宁说是历史、是社会强迫他自觉自愿地当了一个“文化回归者”的形象。黑娃的回归是革命文化的失败和反动文化的胜利,他的文化回归是绝非偶然的,它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总有一个革命——失败——再革命直到成功的文化反复。正由于此,反动文化对黑娃的征服就成了黑娃新的觉醒和革命的文化前导,也就成了黑娃重新走向文化反叛的历史必然理由。鹿兆鹏回来了,他的理论重新唤发了黑娃的革命热情,再一次明确了黑娃的文化信仰,于是,他又一次开始反叛封建文化,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革命成功了,白鹿原人被解放了,但是,经过多种历史磨难和文化考验的黑娃,却被白孝文——这个投机革命的政客文化人所残害。他的最终文化结局的确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但这又是合乎情理的,这进一步说明了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由于此,他的文化反叛——文化回归——文化反叛,直到最后的文化遇难,才显示出一种崇高和悲壮的文化韵味。无疑,黑娃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位“文化回归者”形象,但是,他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文化回归者”形象。这一点,作者没有交代,也不可能交代。中国是个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古老、丰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落后、反动的封建文化已经存活了几千年,而且那些糟粕文化生命力极强,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回归。无疑,黑娃形象给我们的启迪和思索是显而易见的,他使我们站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去反思我们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
7.文化复仇女神田小蛾
《白鹿原》中,田小蛾是一位最具有人文魅力的人物形象。她的坎坷命运,注定要使她成为一个封建宗教社会中的文化复仇女神形象。正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给予于她太多的命运不公,才使她在成为郭举人小老婆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泻欲泡枣的工具。风华正茂的年月,她空守闺房,备受冷落。终于,青春的火焰,使她为黑娃燃烧,就象干柴遇见了火药,两个年轻胴体的接触,释放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妍丽人生光华。这是一次次生命本体意识与封建伦理道德理想的意志较量,爱情的燃烧,使落后的道德一次次望而却步。然后,这种境况是暂时的,当他们二人的事迹败露后,郭举人的一纸休书,虽然成全了她和黑娃,但却将她的命运永远推向了白鹿原的历史文化漩涡。首先给她以沉重打击的是她和黑娃的婚事,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祠堂所拒绝,然后是她被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所奴役的公公鹿三所否认,白鹿村的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万般无奈之中,他和黑娃只好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辛酸岁月。从文化学角度去阐释,小蛾与黑娃的离群索居,实际是作为文化个体的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疏离和遗弃,是他们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回避和遗忘。但是,究其实质,它实际体现了封建宗法社会与人性的格格不入和水火不溶。它说明,那个残酷反动的文化社会,它在抹杀人性的同时,已经到了被人性所唾弃的地步。尽管从潜意识上讲,黑娃和小蛾还是希望被这个反动社会容纳的。但是,这个社会的残忍性正在于此。它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相容任何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的有越轨举动的文化人。正由此,它将小蛾和黑娃推向了一种文化绝境:要么屈从,要么背叛,屈从既已不可能,反叛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小蛾和黑娃远望着那个对他们的爱情充满敌意的宗法社会,远望着那个将他们吞噬和异化的旧秩序,心中充满了绝望、愤怒和悲伤,他们知道,他们成了这个社会的多余人和弃儿,琅琅乾坤,竟无他们的安身之所,他们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里,注定要有大风大浪在肆虐。小蛾是不幸的,一方面她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她还不得不对付那些虚伪的封建卫道士者们的性骚扰;而且,要命的是为了生存。她还要不时承受那来自各方的文化威胁、利诱和陷害。为了营救心爱的黑娃,面容姣好、心地善良的她,中了鹿子霖的圈套,成了鹿子霖满足淫欲的猎物。事情还不仅于此,最严重的是鹿子霖巧设美人计,还要让她成为拉白孝文下水的同谋。谁知道,鹿子霖所想的竟恰恰是她一直想做的,正迎合了她要报复这个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用意。于是,她心甘情愿地堕落了,她在报复了那个万恶社会的同时,也为那个社会扼杀她提供了充分的文化理由。她这个勇敢的文化复仇女神啊,从此注定要在弱小、孤独和痛苦的复仇中,招致到更大的社会报复和文化惩罚,直到最后酿成她人生命运的悲剧和灾难。鹿三一气之下,害死了小蛾,小蛾真正成了被反动社会屈死的冤魂。然而,小蛾这个冤魂仍然是自由的,不可征服的,她作了鬼还要复仇,她让自己的冤魂附着在鹿三身上,借鹿三之口,道出了她的冤屈和不妥协。于是,她化成了成千上万只彩色蝴蝶,向世人不断揭示着社会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她是一个美丽的精灵,是一个永远要复仇的精灵,即使让那些被激怒了的封建宗德秩序的卫道士者们,将她绿色的骨殖烧个干净也在所不辞,即使让那些卫道士们将她的骨粉压倒在六棱塔下,她还是要复仇。她并非象那些封建卫道士所想的那样“永远不能翻身”,正是她印证了白嘉轩在修庙与建塔争论中所说的那句话:“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正是她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的“人妖”、“鬼神”文化力量,变成了“荸荠一样大小的绿头苍蝇”,让白鹿原上那些愚昧的人们坐卧不宁。她一次次进行着新的文化复仇行动,她战胜了法官,一度使瘟疫后的白鹿原撒满了祭奠她的黄裱纸灰烬;正是她,使鹿三很快变得衰老,最后竟至痴呆;正是她,使白嘉轩这样意志坚强、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封建卫道士,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颤粟;也是她,使鹿子霖这样坚强的封建伪君子,变成了神经病,最后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悲惨地死去……。田小蛾,这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生命永恒的文化复仇女神啊,其实她才是真正的人,才是有着伟大人格魅力的人。而那些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的封建卫道士们,其实才是真正的“人妖”和“鬼神”,当他们将小蛾这样的女性诬陷为“人妖”和“鬼神”的时候,这正恰恰说明他们的“人妖”和“鬼神”本质,也正恰恰揭示出这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吃人社会虚伪、残酷,无公平、正义可言。从表面上看,小蛾的复仇行动失败了,固为她的肉体被消失了。但从本质上言,她是最后的胜利者。以一个弱女子,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从物,她竟将那个荒谬宣扬君权、父权、夫权和神权的封建宗法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永无宁日,这足以说明她的伟大。正是她,让那个社会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后人所憎恶,所警惕。这是何等壮观的英雄历史壮举啊,这个壮举正是由她——田小蛾——这个文化复仇女神创造出来的,它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铭记:封建宗法社会是造成我们民族不幸的历史文化根源,只有不断地向这个落后和残忍的封建社会制度进行反抗和复仇,才能拯救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8.文化殉葬者鹿三
这是一个善良、忠厚、勤劳、质朴的老人,生活的重负和无休止的劳作,不曾压弯他的意志,不曾改变他的本色。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象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农人一样,他默默地出生,默默地活,最后再默默地死。他只知道,他是个农民,是个长工,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和生活,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社会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即使被这个社会所戕害也在所不惜。他是一个长工,他注定要为掌柜的干活,尽管他被白嘉轩亲切地称为三哥,甚至平常还和白嘉轩同吃同住。但是,长工就是长工,任何表面的平等都掩盖不了他与白嘉轩仆与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社会本质。他是一个好庄稼汉,他不因自己的这点能耐而喜形于色,更不因自己和掌柜的关系亲密而忘忽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正因为这样,在他身上,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朴实无华和诚实可信之类的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他们生活就象一条平铺直叙的河流在无声地流淌,但是,正是在平平淡淡中,他不断地实践着自己的劳动价值。他是渺小的,这是因为他的渺小几乎使历史本身可以忽略了他,但是,历史并不能因为他的渺小可以真正地忽略了他,因为,正是成千上万象他这样的农民,几千年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历史的航道和生活的航线。他的一生都是在默默无闻中渡过的,他一生唯一一件轰轰烈烈的壮举是杀了他的儿媳妇田小蛾。他是愚昧的,使他竟至糊涂得可悲,他无力为儿子黑娃娶个媳妇,但是,当黑娃领回田小蛾,他又毫不犹豫拒绝了黑娃的婚事。他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毒化,在他的意识中,却总能掂量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轻重。为了那可怕的伦理道德,他竟以葬送儿子和儿媳妇的幸福为代价。他是残忍的,这是因为残忍的封建宗法社会赐予了他这种残忍,而他竟然还认为,这种残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真理。于是,他自觉自愿地成为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卫道士和文化工具,成为扼杀离经叛道者的急先锋,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也为例外。但是,人毕竟是人,任何道德理性都不可能完全否定掉人性本身。正因为如此,当害死小蛾之后,一种人性的负罪感油然而生,而且这种负罪感时时折磨着他软弱、怯懦的灵魂。于是,终于有一天,他孱弱的身躯,再也承受不了那令他窒息的负罪感了,因而,当小蛾的魂灵附入他的体后,他变傻了,得了不可救药的老年痴呆症。白嘉轩说:“三哥老了”,这不是指生理意义上鹿三生命的衰老,而是指社会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他的社会生命的衰老,是文化意义上,鹿三这个文化个体命运的衰老。他在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残害了小蛾的同时,也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残害了自己,他使自己真正成为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牺牲品和文化殉葬品。毫无疑问,鹿三这个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长工形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可能成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秩序的“最后一个长工形象”。他的死亡,意味着成千上万象他一样的中国农民的即将觉醒,也意味着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历史岁月中,作封建社会文化长工的落后传统文化意识已日趋不得人心。鹿三随着他所殉葬的那个社会、文化、时代去了,正是因为他的殉葬唤醒了后人,唤醒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曙光。
《白鹿原》中,象鹿三这样的文化殉葬者不止一个,象兆鹏媳妇,也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殉葬品,她的性错乱以及对鹿子霖违背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变态情恋,都是由封建宗法社会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文化传统造成的。她和鹿子霖的“麦草”之争,不是简单的人性与兽性之争,不是简单的人性与理性之争,而是人类固有的追求幸福的文化愿望,与残酷无情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文化价值之争,她在这个社会中不时寻找着“爱”,然而,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她提供“爱”,而且误导着她的爱,摧残着她的爱、毁灭着她的爱。于是,当她将“爱”和“欲”混淆在一起后,当她将“性”对象错了人时,她得了“花痴”。就注定拥有了不可躲避的悲剧人生结局。显然,是传统的落后的封建婚姻观念对她的压抑和窒息,导致了她的“花痴”。于是,这朵痴情的美丽的人生之花,还没盛开,就被摧残凋谢了。由于她神经错乱,胡言乱语,有伤风化,终于,她被当民间名医的父亲冷先生下药毒了。父辈文化创造了她,父辈文化又毁灭了她,父辈文化,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奇特社会文化角色,令我们深思。是的,传统的封建文化,不正是这样一种“父辈文化”吗?正是它,在创造我们子孙后代文化生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戕杀着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所象征的新文化。面对这样残酷无情的反动文化,我们后人,能不作“杀父弑君”的文化忤逆之子吗?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太丰富了,除了以上我们论述的文化形象,还有岳维山、田福贤、贺老九、仙草等,都不乏独特的文化魅力,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分析论述了。总之,小小的《白鹿原》,是一个大大的历史舞台,它使无数文化过客,成为历史烟云,尽管这些过客都曾徒劳地表现过自己的生命本体意识,都曾坚韧地寻找过自己人生的文化突破口。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并且被淹没在封建宗法社会所设制的腐朽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大染缸中。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都是失败者,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灾难和不幸。如果说,他们的一生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只是找到了“生命的苦难与悲凉”。
[注释]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回第三卷第五十一节,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编)第五十一节。
2.[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第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 《白鹿原》引文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此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说不尽的“白鹿原”》)
附:
张亚斌研究员简介

张亚斌
张亚斌,男,陕西合阳人,1963年4月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198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7月毕业后分配至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工作。2003年4——7月,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2007年3月被引进至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现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教育研究所、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副主编,文法部中文专业责任教师。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丛书”编委,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民进陕西省第九届科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高校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会秘书长,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专业、电视节目制作专业责任教师,副编审,副教授。曾兼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社会面面观》主持人节目兼职编辑、记者,西安电视台《长安书画名家展播》栏目编导,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厅《声屏之友》杂志兼职编辑,清华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杂志、《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陕西书画报》、《中国新物业》等杂志的编委,陕西师范大学杂志社第二届期刊质量评委。
曾编导过《吾祖黄帝》、《耀瓷》、《告别筒子楼》、《楷书入门二十讲》、《大学并不遥远》、《步入辉煌》等60多部教学或专题节目,为中文专业、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小教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学生讲授过《广告创意与制作》、《影视批评》、《影视写作》、《电视专题》、《电视新闻》、《广播电视概论》、《电视栏目与策划》、《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应用写作》等10多门课程。
先后参与了中央电大承担教育部规划课题“全国电大教育现状调研” 课题项目(2005)和“全国电大毕业生追踪调查” 课题项目(2005),参与了中央电大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批的国家“十五”规划课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学质量保证的研究”课题项目(2003)、中央电大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现代远程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子课题:现代远程教育环境下的职业教学模式研究”课题项目(2005)、陕西省教育厅批准的“陕西省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研究项目 “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模式定位研究”课题项目(2004)、中央电大和陕西电大承担的“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学习支持服务的研究与实践”课题项目(2002)“电大远程开放素质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2002)课题项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承担的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生态文化理论视野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研究”课题(200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生态文化视域下当代文学的新乡土叙事比较研究”课题(2011)。
参加了北京市“十一五”规划课题“基于网络条件下构建首都社区学习环境的研究”课题项目(2007)、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首都市民终身学习公共资源平台研究”课题项目(2007)、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现代远程教育环境下电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项目(2006);参与了中央电大咨询改革发展委员会承担的 “中国电大教育的定位与电大系统建设”课题研究项目(2007),主持了中央电大和高校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现代远程教育合作文化研究”课题项目(2007),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承担的“国家开放大学的社会责任研究”项目(2011),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基地远程教育研究中心的“开放大学的文化研究”项目(2011)等。
截至目前,参与科研课题15个。撰写完成了《电大远程开放素质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西部广播电视大学现状调研报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现状调研报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追踪调查报告》、《从学习型城市发展看城市电大发展走向》、《首都市民终身学习需求情况调查研究报告》《首都居民社区学习环境的情况调查报告》、《开放大学的模式建构、责任担当和文化使命——加拿大远程教育的考察研究报告》等一系列课题或项目报告。
曾在《中国电化教育》、《中国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唐都学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陕西教育学院学报》、《西安石油学院学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电视剧》、《荧屏世界》、《艺术界》、《西北美术》、《陕西书画报》等刊物上发表远程教育学、文学、影视艺术学、美术史、美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论文15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论文8篇(文学论文1篇,美术史论文1篇、影视学论文1篇、远程教育论文5篇)。
出版有个人专著《影视艺术鉴赏通论》(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9月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5月第1版)和论文集《远程教育文化现象学研究》(中央电大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其中,《影视艺术鉴赏通论》一书被许多大学选为影视专业的课程教材、中文专业的课程教材或其他专业的通识课程教材,并被教育部遴选为国家精品资源课程教材。与此同时,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远程教育史的著作《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担任清华大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材《远程教育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的第一副主编。参与了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本科生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的编写,参编的著作还有《成人教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成人教育心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文学评论集《〈秦腔〉大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月第1版)、《实用美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月第1版)、《实用网络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月第1版)等。
先后十多次在有关国际远程开放教育学术会议宣读或交流论文,其中,在“第21届国际远程教育协会世界大会”宣读的论文《孤独的远程社会学习者:在网络里寻求终身的学习支援》,受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 Gunawardena博士高度评价,并被其弟子Kerrin Barrett女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引用,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年会交流、宣读论文4次(第13、16、21、23届)。2004年4月18日——22日,陪同民进中央王佐书副主席一行在陕西进行高等教育调研。2010年3月,访问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卡尔顿大学、渥太华大学、麦吉尔大学、康考地亚大学、阿萨巴斯卡大学、皇道大学等8所大学和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并与这些学校的专家进行了远程教育的学术交流。
个人论文、著作等科研成果先后获得过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评比”一等奖、“‘海尔杯’全国远程教育论文评比”一等奖、第七届全国成人教育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二等奖、“陕西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三等奖、“陕西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三等奖、陕西省教育技术成果评比一等奖、陕西省成人教育研究成果评比一等奖等奖励共计20余项,累计发表论文成果100多万字。
文学创作方面,曾在《延河》、《农民文学》、《西安晚报》等有关报刊杂志媒体上,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艺术作品,其诗作曾被选入《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中国当代校园诗人选萃》、《当代校园诗赏析》等书中,报告文学被选入《三秦之光》报告文学集中。
由于在工作中的突出成绩,1997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电教工作者”,1998年,被评为“全国电化教育优秀工作者”,1999年,个人辞条被收入香港公开大学遥距及成人教育研究中心“亚洲远程教育/高等成人教育研究专家名录”,之后,个人辞条又被收入国家人事部专家服务中心编写的《中国专家大辞典》第七卷中。2001年个人资料又被收入由教育部电教办、总参电教局和中国电化教育协会支持建设的、由《教育技术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教育技术专家信息库”“教育技术”网站中。2008——2009年,又入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和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学科专家库。
2002年,被北京师范大学授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突出贡献奖”,2004年,在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年终考核时,被评为“优秀处长”,2007年被民进陕西省委评为“模范会员”。 |